陈建设作为当代豫剧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以其扎实的唱功、细腻的表演和对传统剧目的创新演绎,在舞台上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其中由他领衔主演的《白马告状》堪称其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经典豫剧传统剧目,经过陈建设及其团队的精心打磨,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审美,成为豫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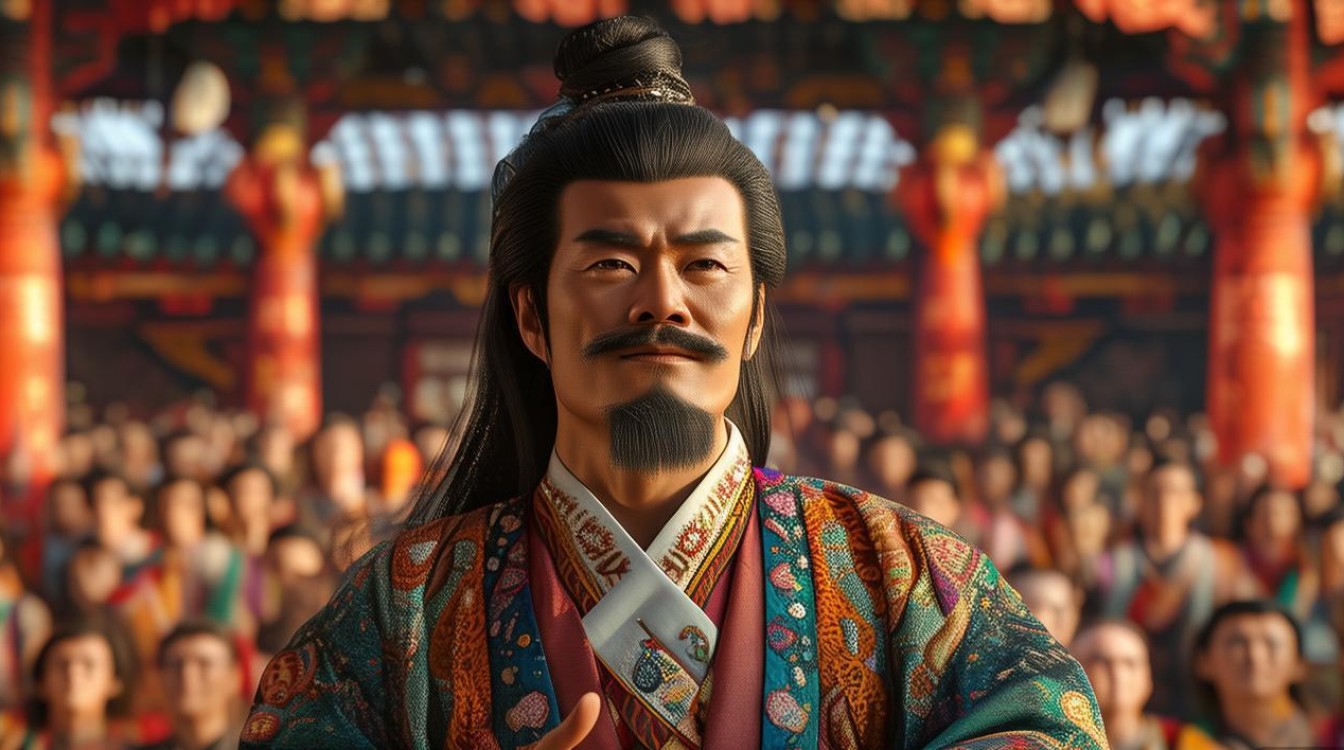
《白马告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古代,讲述了书生李文龙与妻子张玉莲遭遇奸人陷害,家破人亡后,李文龙的魂灵附于白马身上,向包公告状,最终沉冤得雪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冤情”为主线,通过“遭陷害—魂告状—明真相—惩恶人”的情节推进,展现了古代社会底层百姓在黑暗统治下的苦难,以及对正义的执着追求,陈建设在剧中饰演的李文龙,从温文尔雅的书生到含冤而死的悲情角色,再到魂魄附白马时的愤懑与不甘,其表演层次分明,情感饱满,尤其在“白马告状”的核心场次中,他通过眼神的凝滞、身段的僵硬与唱腔的撕裂感,将一个冤魂的绝望与呐喊演绎得淋漓尽致,令观众动容。
作为一部传统剧目,《白马告状》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曲折的剧情,更在于其独特的戏曲程式与音乐表现,豫剧以其高亢激越、贴近生活的唱腔著称,而《白马告状》在音乐设计上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陈建设的唱腔兼具豫东调的刚健与豫西调的深沉,在“诉冤”唱段中,他运用“慢板”的舒缓铺垫悲情,再以“二八板”的节奏加快,最后通过“飞板”的爆发式高音,将李文龙积压已久的愤懑推向高潮,形成了“先抑后扬、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剧中“白马”的形象设计也别具匠心,传统戏曲中马的形象多通过马鞭、虚拟动作表现,而《白马告状》中,陈建设结合了舞蹈与武打元素,通过身段的腾挪翻转、步法的轻盈灵动,配合灯光与音效的烘托,将白马的“灵性”与“神威”展现得栩栩如生,既有传统写意之美,又具现代舞台冲击力。
该剧的舞台呈现同样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布景设计上,摒弃了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模式,转而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公堂的庄重、荒郊的凄凉、阴森的阎罗殿等场景,通过灯光的明暗变化、背景纱幕的投影,营造出层次分明的空间感,既保留了戏曲的“写意”本质,又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服装方面,李文龙的青衫、张玉莲的素衣、包公的黑蟒等,均遵循传统戏曲的服饰规范,同时在面料与纹饰上融入现代工艺,使角色形象更加鲜明立体,这些创新并非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活化”,让经典剧目在当代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白马告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还在于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普世价值,剧中“冤情昭雪”的情节,寄托了古代百姓对“清官政治”的向往,而李文龙“虽死不屈”的精神,则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正义的坚守,陈建设在演绎这一角色时,不仅注重外在的表演技巧,更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将个人的悲剧与时代的黑暗相结合,赋予角色超越时代的意义,正是这种对人性与正义的深刻诠释,使得《白马告状》在不同时代都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成为豫剧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典范。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陈建设在《白马告状》中塑造的李文龙角色,有哪些独特的表演细节?
解答:陈建设塑造的李文龙角色,在表演细节上注重“内外兼修”,在外在技巧上,他通过眼神的变化展现人物命运:前期是书生的清澈明亮,中期遭陷害后的绝望迷茫,后期魂魄附身时的怨毒与不甘,身段上,他借鉴了武生的“靠腿”“旋子”等动作,在“白马驰奔”段落中,以轻盈的跳跃与急促的翻身,表现白马的急切与愤怒,在唱腔处理上,他创新性地在“哭板”中加入“泣音”,模仿哭腔的哽咽感,使“冤枉”二字更具穿透力,内在情感上,他强调“悲而不伤,怒而不狂”,通过微表情的克制(如咬紧的牙关、颤抖的双手)传递人物的隐忍与爆发,使角色既有传统文人的风骨,又具普通人的悲情,让观众共情。
问题2:《白马告状》作为传统剧目,在当代演出中如何平衡“守正”与“创新”?
解答:《白马告状》的当代演出,在“守正”方面严格遵循豫剧的艺术规范:保留核心唱腔的板式结构(如【二八板】【慢板】)、传统程式动作(如“跪步”“甩发”)以及“一桌二椅”的舞台美学,确保剧种的“根”与“魂”不变,在“创新”上,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音乐配器,在传统板胡、梆子的基础上,加入交响乐元素,增强音乐的层次感;二是舞台技术,运用多媒体投影展现“阴曹地府”“公堂威严”等场景,用灯光切割空间,强化戏剧冲突;三是叙事节奏,通过压缩次要情节、突出“告状”核心场次,使剧情更紧凑,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这种“守正创新”的平衡,既让老观众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关注,实现了经典剧代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