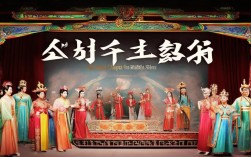马连良先生是京剧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四大须生”之一,他以“潇洒飘逸”的台风、“巧俏脆帅”的唱念风格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马派”,其艺术生涯横跨民国与新中国时期,剧目涵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及少量现代戏,几乎重塑了京剧老生行的表演范式,从科班启蒙到挑班成派,从传承经典到创新突破,马连良的“全剧”不仅是剧目的集合,更是一部浓缩的京剧生行艺术发展史。

艺术特色:马派艺术的“破”与“立”
马连良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对传统的“破”与“立”,他早年师从刘景然、蔡荣桂等,宗法“谭派”(谭鑫培),又不拘泥于模仿,而是吸收余叔岩的“脑后音”、高庆奎的“黄钟大吕”,甚至借鉴老旦、花脸的唱腔技巧,创造出“收放自如、刚柔相济”的独特唱法,其念白被誉为“千斤白,四两唱”,无论是京白的抑扬顿挫,还是韵白的抑扬顿挫,都融入了生活化的语感,如《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的念白,既有老成持重,又有思乡的缠绵,被称为“马派白口”的范本。
表演上,马连良突破了老生“重唱轻做”的局限,将身段、表情、台步融为一体,形成“帅、脆、巧”的风格,他的台步如《定军山》中“斩夏侯”的跨腿亮相,既显武将威风,又含文士儒雅;眼神运用更是出神入化,《三顾茅庐》中“隆中对”一段,通过眼神的流转展现诸葛亮的运筹帷幄,服装扮相上,他大胆改良蟒袍、靠旗的样式,使服饰更贴合人物身份,如《赵氏孤儿》中程婴的素衣褶子,既显平民质朴,又暗藏悲壮色彩,这种“为人物服务”的创新,对后世京剧舞台美术影响深远。
剧目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艺术轨迹
马连良的剧目浩繁,按题材和创作时期可分为传统骨子老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类,每一类都体现了他对“戏以人传,人以戏立”的深刻理解。
传统戏:经典的“重塑者”
传统戏是马连良艺术的根基,但他并非简单复刻,而是在继承中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 《定军山》:这出谭鑫培的“看家戏”,马连良演出了“老戏新做”,黄忠的“请缥”“斩夏侯”等场次,他弱化了纯武功展示,强化了老将不服老的豪迈与智勇双全的谋略,唱腔“这一封书信来得巧”既保留谭派的苍劲,又加入了马派的“俏音”,使人物更鲜活。
- 《群英会·借东风》:这是马连良与周信芳、叶盛兰等合作的巅峰之作,他在“借东风”中饰演的诸葛亮,一改“羽扇纶巾”的程式化扮相,通过稳健的台步、沉静的眼神和“风萧萧”唱段的悠扬拖腔,塑造了“智绝”而非“神绝”的军师形象,设坛台祭东风”的念白,节奏如行云流水,被誉为“一字一珠”。
- 《捉放曹》:陈宫的“行路”和“宿店”是马派念白的重头戏,他通过“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的唱段,将陈宫从愤怒、悔恨到矛盾的心理变化,用“擞音”“颤音”细腻呈现,尤其是“宿店”中“杀贼”的爆发与“心慌意乱”的收束,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
新编历史戏:时代的“践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积极参与新编历史戏创作,将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结合。
- 《赵氏孤儿》:他饰演程婴,突破了传统老生的“忠臣”脸谱,赋予其“忍辱负重、大义灭亲”的复杂人性,唱腔“白虎堂奉了命”借鉴了梆子戏的激越,念白加入口语化的“顿挫”,使程婴从“义士”升华为“平民英雄”,该剧成为新编历史戏的典范。
- 《状元媒》:寇准一角被他演绎得“智趣并存”。“接驸马”一场的念白,既保留官员的庄重,又加入诙谐的“京片子”,唱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融合了老生与老旦的唱法,开创了“老生唱腔女性化”的先河,至今仍是马派弟子的必修课。
现代戏:探索的“先行者”
尽管马连良的艺术以传统为主,但在现代京剧领域,他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1964年,他在现代戏《杜鹃山》中饰演郑老万,这是京剧舞台上少见的“老农民”形象,他深入生活,学习农民的步态和语言,将老生的“髯口功”与农民的“挑担”动作结合,唱腔“家住安源”借鉴了江西采茶戏的旋律,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生活气息,尽管现代戏并非其艺术主流,但这种“跨界”尝试,体现了京剧艺术家对艺术创新的坚守。
重要剧目概览(表格)
| 剧目类型 | 剧目名称 | 角色 | 艺术亮点 |
|---|---|---|---|
| 传统戏 | 《定军山》 | 黄忠 | 唱腔“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巧俏结合,身段“斩夏侯”显老将豪迈 |
| 传统戏 | 《借东风》 | 诸葛亮 | 念白“设坛台”如行云流水,眼神运筹帷幄,台风沉稳潇洒 |
| 传统戏 | 《捉放曹》 | 陈宫 | 念白“听他言”展现心理变化,唱腔“心慌意乱”情感张力强 |
| 新编历史戏 | 《赵氏孤儿》 | 程婴 | 唱腔“白虎堂”融入梆子戏,念白口语化,塑造平民英雄形象 |
| 新编历史戏 | 《状元媒》 | 寇准 | 唱段“自那日”融合老生老旦,念白诙谐庄重并存,开创“智趣”风格 |
| 现代戏 | 《杜鹃山》 | 郑老万 | 唱腔“家住安源”借鉴采茶戏,步态语言生活化,探索老生现代形象 |
影响与传承
马连良的艺术不仅影响了京剧生行,更推动了京剧艺术的现代化进程,他的“马派”弟子遍及全国,如马长礼、张学津、冯志孝等,均成为当代京剧的中坚力量;其剧目《借东风》《赵氏孤儿》等至今仍是舞台常演剧目,唱腔、念白被奉为“圭臬”,更重要的是,他“尊重传统、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为京剧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京剧既要扎根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才能在舞台上永葆生命力。

相关问答FAQs
Q1:马连良的“马派”艺术与其他须生流派(如谭派、余派)有何区别?
A1:马派与谭派、余派同属老生行,但风格差异显著,谭派(谭鑫培)以“灵活多变”著称,余派(余叔岩)以“醇厚刚劲”见长,而马派则突出“潇洒飘逸、巧俏脆帅”,具体而言,唱腔上,马派更注重“俏音”和“节奏变化”,如《借东风》的拖腔比谭派更舒展,比余派更灵动;念白上,马派融入更多生活化语感,如《群英会》中诸葛亮的念白,既有韵白的抑扬顿挫,又有京白的自然流畅;表演上,马派打破“重唱轻做”的局限,将身段、表情与人物性格紧密结合,形成“帅、脆、巧”的独特台风,这是其他流派所不具备的。
Q2:马连良在现代京剧创作中有哪些探索?这些探索对京剧发展有何意义?
A2:马连良在现代京剧领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角色类型的突破,如《杜鹃山》中饰演的农民郑老万,打破了传统老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角色局限;二是表演语言的创新,他深入生活,学习农民的步态、语言和唱腔,将传统老生的“髯口功”“台步”与生活化的动作结合,唱腔中融入地方戏曲(如江西采茶戏)的旋律,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拓宽了京剧现代戏的表现路径,证明了京剧艺术不仅可以表现历史题材,也能生动刻画现代人物,为京剧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实践范例,影响了后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戏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