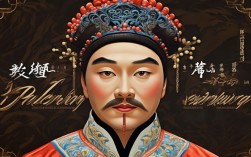闫立品是豫剧艺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闺门旦表演艺术家,其艺术成就不仅在于醇厚婉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更在于她对戏曲文本的深度解读与创造性转化——“观文”二字,恰是她艺术创作的核心方法论,她曾说:“演戏如作画,先要读懂画中意;唱戏似吟诗,必知诗里藏真情。”这种以文本为根基、以人物为核心的创作理念,让她的表演既有传统戏曲的程式之美,又充满直抵人心的情感张力。

闫立品的“观文”,首先体现在对剧本的敬畏与深耕,她从不满足于表面的台词与情节,而是像研读经典著作般逐字推敲剧本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与潜台词,在排演《秦雪梅》时,她不仅反复研读明清传奇《商辂》原著,还查阅明代妇女生活史料,甚至走访河南乡间的贞节牌坊,试图理解秦雪梅在“贞烈”与“深情”双重枷锁下的心理挣扎,她曾对弟子说:“秦雪梅不是‘哭坟的符号’,是‘被礼教吃掉的活人’——她读丈夫遗书时的手抖,不是演出来的,是心疼到骨头缝里的颤。”这种对文本细节的极致挖掘,让她的表演超越了“行当”的局限,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
“观文”意味着将文本内核转化为可感的舞台语言,闫立品认为,戏曲的“文”不仅是文字,更是“情”与“境”的融合,在《秦香莲》中,“见皇姑”一场,剧本仅写“秦香莲上前辩理”,她却通过眼神的层次变化传递文本未尽的悲愤:初见皇姑时的怯懦(低垂的眼睑、微颤的指尖),听其刁难时的隐忍(攥紧衣袖、强咽泪水),提及儿女时的决绝(猛抬下巴、泪中带火),这种“以形写神”的处理,让文本中的“忠贞冤屈”具象化为观众能“看见”的情感冲突,她的唱腔亦是如此,《秦雪梅吊孝》中“观文见你遗墨在”一句,她根据文本中“见遗墨如见人”的设定,将“遗墨”二字唱得轻而碎,尾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仿佛墨迹未干,人已天涯,让文字背后的思念与痛楚穿透时空。
闫立品的“观文”还体现在对传统文本的创造性革新,她不盲从旧本中的“脸谱化”设定,而是以现代视角赋予人物新的解读,在《蝴蝶杯》中,传统演出将田玉川与胡凤莲的爱情处理为“才子佳人”模式,她则通过文本细读,突出“藏杯”一场中胡凤莲的机智与勇敢——当田玉川藏杯时,她故意佯装不知,却在转身后用眼角余光观察,既表现了少女的羞涩,又暗含对“反叛父权”的认同,这种对文本潜力的挖掘,让传统剧目在保持韵味的同时,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力。

她的艺术实践证明,“观文”不是被动的文本复述,而是主动的“二次创作”,正如戏剧理论家张庚所言:“立品演戏,是把‘死剧本’唱成了‘活人生’。”这种从文本到舞台的转化能力,正是她成为豫剧“闫派”创始人、被观众誉为“豫剧的程砚秋”的关键所在。
| 剧目 | 核心文本冲突 | 闫立品的处理方式 | 艺术效果 |
|---|---|---|---|
| 《秦雪梅》 | 贞烈与深情的矛盾 | “哭坟”唱段用“慢板转流水板”,声腔从哽咽到激昂 | 展现人物刚烈外表下的柔情,催人泪下 |
| 《秦香莲》 | 底层忠贞与权贵压迫的对抗 | “见皇姑”时眼神从躲闪到坚定,身段由屈到挺 | 凸显人物“宁折不弯”的品格,引发共情 |
| 《蝴蝶杯》 | 个人情感与家族礼教的冲突 | “藏杯”中通过眼神躲闪与偷看,表现少女的勇敢与羞涩 | 打破“才子佳人”模式,人物更立体 |
闫立品的“观文”理念,对当代戏曲传承仍有深刻启示,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她的“慢功夫”——逐字推敲文本、深入生活体验、以情化形的表演,提醒我们:戏曲的根,永远扎在“人”与“情”的土壤里,只有读懂了文本的“魂”,才能让程式的“形”真正活起来,让百年豫剧在新时代继续唱响动人的故事。
FAQs
Q1:闫立品的“观文”理念与当代戏曲演员的文本解读有何不同?
A:闫立品强调“生活体验+文本细读”,会结合自身经历与历史背景理解人物,如为演《秦香莲》走访古代妇女;当代演员更依赖导演解读或多媒体资料,有时缺乏对文本的独立思考,易导致表演表面化。

Q2:如何理解闫立品“演人要演心”的艺术主张?
A:她认为表演不仅要模仿人物言行,更要挖掘内心动机——通过眼神、唱腔等细节传递真实情感,如《秦雪梅》中“观文见你遗墨在”的哽咽唱腔,让观众“看见”人物的灵魂,而非仅看到“戏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