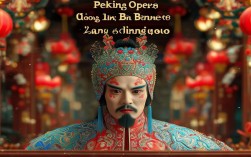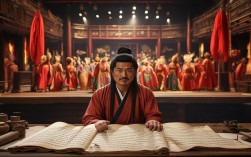张宝英作为豫剧“常派”艺术的杰出传人,以醇厚饱满的唱腔、细腻深沉的表演塑造了众多经典舞台形象,断桥》中“恨上来”的情感爆发,堪称其艺术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点睛之笔”,这一片段出自《白蛇传》,白娘子历经劫难与许仙断桥重逢,面对负心人的愧疚与误解,积压的委屈、愤怒与爱恨交织的情绪如洪水般倾泻,“恨上来”三字既是情感的宣泄口,也是人物性格与演员功力的集中展现。

《断桥》一剧以“情”为骨,以“恨”为魂,而“恨上来”则是白娘子情感链条的顶点,剧情中,白娘子为救许仙水漫金山,触犯天条,被压雷峰塔前;许仙受法海蛊惑,以为妻子是妖,断桥重逢时满心惶恐与悔恨,张宝英演绎的白娘子,初见许仙时眼神中仍有未消的爱意,但当听到“你本是凡间一女子,怎敢与佛祖来抗衡”的指责,积压的委屈瞬间转为悲愤——“恨上来”的唱段便在这情感张力达到顶点的时刻爆发,她的演唱并非单纯的怒吼,而是将“恨”拆解为“痛”“怨”“怒”“悲”的多重层次,通过豫剧独特的“豫东调”与“豫西调”融合,让声腔如刀刻般精准传递人物内心。
从表演技法看,“恨上来”的呈现是唱、念、做、舞的高度统一,张宝英的嗓音兼具“脑后音”的穿透力与“胸腔音”的厚重感,起腔时用“哭腔”铺垫,字头轻咬、字腹延展、字尾收束如抽丝,一句“恨上来未语泪满腮”,未开口已闻哽咽,泪珠随颤音滚落,瞬间将观众带入情境,随后板式由【二八板】转为【快二八】,节奏陡然加快,咬字如珠玉迸溅,“你听信谗言把心改,夫妻情分你丢脑外”,每句尾音都带着愤懑的颤音,配合水袖的“甩、挑、扬”,时而掩面悲泣,时而指向许仙控诉,身段如风中柳絮般摇曳,却又暗藏刚烈不屈的劲道,尤其是“断桥未断人肠断”的拖腔,她运用“偷气”“换气”的技巧,让声音在高低起伏中似断非断,恰如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恨意,唱至“恨只恨法海老贼设毒计”时,突然拔高至最高音,如惊雷炸响,将“恨”的爆发力推向极致,却又在收尾时转为低沉的叹息,留下无尽的苍凉。
张宝英对“恨上来”的诠释,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深入挖掘了人物的文化心理,白娘子的“恨”,本质是“情”的反面——她对许仙的爱至深至纯,故被辜负时的痛才锥心刺骨;她为救夫不惜与天庭对抗,却被视为“妖孽”,这种不被世俗理解的委屈,让“恨”中多了份悲壮,张宝英在表演中特别注重“眼神”的运用,从初见时的“含情脉脉”,到质问时的“怒目圆睁”,再到绝望时的“黯然神伤”,眼神的流转如微雕般细腻,让观众从目光中读懂白娘子“爱之深、责之切”的复杂心绪,这种“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表演,正是常派艺术“圆、润、厚、唱”精髓的体现,她将豫剧的“唱功”与“做功”熔铸为一,让“恨上来”不仅是一段唱腔,更成为人物灵魂的呐喊。

从艺术传承看,“恨上来”的演绎见证了张宝英对常派艺术的守正创新,常香玉先生曾强调“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张宝英在继承常派“吐字清晰、韵味醇厚”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对唱腔节奏进行了调整:传统演绎中“恨上来”的拖腔较长,她则适当缩短过渡,增强爆发力的同时保留豫剧的“中州韵”;身段设计上,她在保留水袖功、台步等传统程式的同时,融入了现代舞蹈的张力,让白娘子的“恨”既有古典戏曲的含蓄,又有直击人心的现代感染力,这种“守其形、传其神、扬其韵”的创新,让“恨上来”这一经典片段在舞台上历久弥新,成为豫剧艺术传承与发展的生动注脚。
“恨上来”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它超越了具体的剧目,成为豫剧表达极致情感的“范式”,张宝英通过这一片段,展现了豫剧不仅能演绎家长里短的温情,更能承载惊心动魄的悲怆;唱腔不仅能“以声传情”,更能“以形塑魂”,她的表演让观众明白,真正的“恨”,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爱到极致后的幻灭,是理想被现实击碎后的呐喊,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共鸣,让“断桥恨上来”成为跨越地域与时代的舞台经典。
“恨上来”情感层次与表演技法对应表
| 情感层次 | 唱腔特点 | 身段动作 | 情感内涵 |
|---|---|---|---|
| 初见悲愤 | 【二八板】起腔,哭腔铺垫,尾音带颤 | 水袖掩面,微微颤抖,眼神含泪 | 被辜负的委屈,爱意未消的痛苦 |
| 痛斥薄情 | 板式加快至【快二八】,咬字铿锵,尾音上扬 | 指向许仙,水袖“甩袖”,肩头耸动 | 对负心人的质问,对情变的愤怒 |
| 绝望控诉 | 拖腔运用“偷气”,音域高低起伏,最高音爆发 | 踉跄后退,望塔长叹,水袖“搭肩” | 对命运的不甘,对爱情的绝望 |
FAQs
问:张宝英在“恨上来”中如何通过“气口”运用增强情感表现力?
答:张宝英在“恨上来”唱段中特别注重“气口”的巧用,例如在“断桥未断人肠断”的长句中,她通过“偷气”(快速吸气而不留痕迹)将句子分为“断桥未断—人肠断”,让“断”字重复时情感层层递进;在“恨只恨法海老贼设毒计”的高音爆发前,她会用“提气”(丹田上提)积蓄力量,使高音既饱满又有穿透力,而收尾时的“沉气”(气息下沉)则让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懑,形成“爆发—收敛”的情感张力,让观众在声腔的起伏中感受到白娘子恨意的强烈与复杂。

问:“断桥恨”中的“恨”与“悲”有什么区别?张宝英如何通过表演区分这两种情绪?
答:“恨”与“悲”虽同为负面情绪,但内核不同:“恨”指向外部的“怨怼”,是对他人或命运的指责;“悲”指向内部的“哀伤”,是对自身遭遇的无奈,张宝英通过眼神、身腔和节奏进行区分:“恨”时眼神如炬,眉峰上挑,唱腔节奏急促,如“你听信谗言把心改”的控诉,字字如刀;“悲”时眼神低垂,嘴角下撇,唱腔放缓,如“断桥未断人肠断”的叹息,拖腔绵长,尤其在“恨上来”的转折处,她会先以“悲”的姿态掩面抽泣,再突然抬头以“恨”的眼神直视许仙,这种情绪的瞬间切换,让“恨”与“悲”在冲突中相互强化,更凸显人物内心的撕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