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与戏曲《伐子都》的创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戏曲改编既需要尊重历史文本的根基,又需要在当代审美语境下寻找新的表达可能,这部剧目以颍考叔与子都的矛盾为核心,展现了嫉妒、背叛与人性挣扎的永恒主题,如何在经典故事中挖掘现代共鸣,成为贯穿创作始终的命题。

创作初期,我们首先聚焦于故事内核的再挖掘,传统版本中,子都的形象多被简化为“因妒杀人”的扁平反派,但团队认为,这种单一的人物设定难以承载戏曲“写意传神”的美学追求,我们尝试从“嫉妒”这一人性弱点切入,将子都的堕落过程具象化为“荣誉焦虑—心理失衡—行为失控—自我毁灭”的递进式轨迹,在“夺帅”一场中,我们通过子都与颍考叔的两次同框对比——一次是校场上颍考叔力举大鼎的英姿,一次是子都暗中攥紧拳头的特写,用肢体语言外化其内心的嫉妒萌芽,而非依赖传统的脸谱化表演,这种处理既保留了戏曲“以形传神”的传统,又让人物动机更具说服力。
人物塑造的立体化,是创作中另一大突破点,颍考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英雄,我们为他增加了“知子都之能而容其短”的细节:在庆功宴上,当众夸赞子都的箭术,甚至在子都暗算他时,仍留下“将军箭法超群,当为国之栋梁”的遗言,这种“以德报怨”的设定,既凸显了颍考叔的君子之风,也反衬出子都嫉妒的荒诞与可悲,而子都的悲剧性,则体现在他对“荣誉”的偏执上——他并非天生恶人,而是将“成为焦点”视为人生唯一价值,当颍考叔的光芒掩盖了他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为此,我们特意设计了“噩梦”一场:子都在幻觉中反复看到颍考叔的身影,舞台灯光由明转暗,配乐中加入扭曲的编钟声,用视听手段表现其内心的煎熬,让观众感受到“嫉妒如毒噬心”的痛苦。
舞台呈现上,我们尝试在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表达间寻找平衡。“战场厮杀”一场,既保留了“翻跟头”“耍花枪”等传统武戏技巧,又通过多媒体投影呈现千军万马的宏大场面——背景屏幕上快速闪过的战旗、飞箭与舞台上的演员动作同步,营造出“虚实相生”的意境,而“子都之死”的高潮戏,我们舍弃了传统“吐血而亡”的程式化表演,改为让子都蜷缩在舞台中央,手中紧握颍考叔赠送的玉佩,灯光逐渐聚焦,最终只留一束追光打在颤抖的手上,配乐以低沉的埙声收尾,用“无声胜有声”的手法表现其内心的彻底崩溃,留给观众更多思考空间。
主题的当代转化是创作的核心目标,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嫉妒、竞争、压力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子都的故事恰好能引发观众对“如何面对竞争”“如何处理负面情绪”的反思,我们在结尾处加入了一段旁白:“嫉妒是人性深渊的镜子,照见他人,也照见自己。”希望通过这种点题,让观众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也能获得对自身生活的启示。

以下是传统版本与创作版本在关键要素上的对比:
| 对比维度 | 传统版本特点 | 创作版本调整 |
|---|---|---|
| 人物动机 | 天生嫉妒,性格扁平 | 荣誉焦虑,心理失衡导致行为 |
| 叙事节奏 | 线性推进,侧重情节冲突 | 增加内心戏,用闪回深化动机 |
| 视觉呈现 | 程式化表演,以虚代实 | 多媒体辅助,虚实结合强化氛围 |
| 主题立意 | 道德训诫,善恶有报 | 人性探索,引发现代共鸣 |
创作《伐子都》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戏曲艺术的致敬,也是对其当代生命力的探索,唯有在尊重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表达方式,才能让经典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FAQs
Q1:创作《伐子都》时,如何平衡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表达?
A1:我们始终坚持“程式为魂,形式为用”的原则,在表演上,保留了“唱念做打”的核心技巧,如子都的“翎子功”表现其得意与焦躁,颍考叔的“靠旗功”凸显其武将风范;在舞台呈现上,则引入多媒体、灯光等现代元素辅助叙事,如用投影展现战场全景,用灯光切换表现人物内心,但这些技术手段始终服务于戏曲的“写意性”,不会喧宾夺主,确保传统戏曲的韵味不受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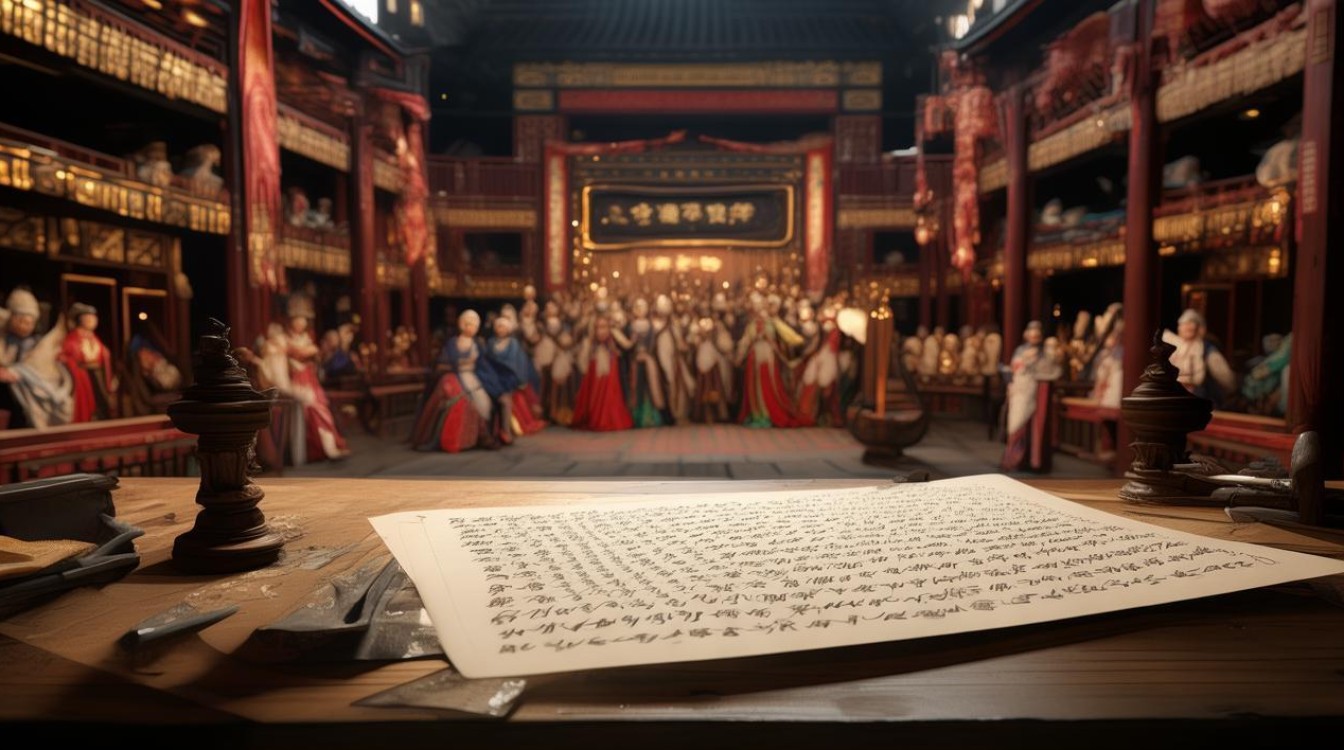
Q2:如何让年轻观众对这部传统剧目产生共鸣?
A2:在人物塑造上挖掘人性共通点,如子都的“嫉妒焦虑”、颍考叔的“包容大度”,这些情感是年轻人也能理解和共情的;在叙事节奏上加快,减少传统戏曲中冗长的唱段,增加紧凑的戏剧冲突,如“校场夺帅”“暗算盟友”等场次用快节奏推进;通过视觉创新吸引注意力,如舞台设计融入现代美学元素,服装在传统基础上加入简洁线条,让年轻观众在熟悉的故事中感受到新鲜的艺术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