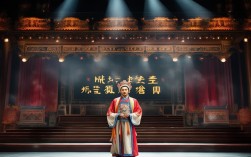豫剧《诸葛亮归天》作为传统经典剧目,其下集以“秋风五丈原”为核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诸葛亮生命终章的悲壮与忠贞,通过“禳星”“托孤”“归天”等关键情节,将一代贤臣的智慧、无奈与遗憾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豫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老戏”之一。

故事开篇即入五丈原军营,时值秋夜,秋风萧瑟,营帐内灯火昏黄,诸葛亮身染重病,伏案于《出师表》手稿前,咳嗽声不断,却仍强撑精神批阅军情,报子来报:“司马懿大军压境,营外擂鼓挑战。”诸葛亮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却仍以空城计之谋稳住军心,命姜维按兵不动,自己则登上七星坛,设下禳星之法——此为全剧最核心的“禳星”情节,豫剧在此处通过细腻的表演艺术,将诸葛亮的“智”与“悲”推向极致:演员身着八卦道袍,手持七星剑,步履蹒跚却眼神坚定,唱腔以苍凉的“慢二八板”开篇,“秋风起兮黄叶飘,五丈原上夜寂寥”,唱词既点明时节,又暗喻生命将逝;坛前步法则融合了“太极步”“云手”等程式化动作,配合低沉的锣鼓点,营造出“与天争命”的紧张氛围,当魏延慌张闯入,不慎扑灭七星灯时,诸葛亮猛然一震,唱腔陡转急促,从“二八板”突入“快二八板”,一句“灯灭星殒天意定,孔明命不久长”,字字泣血,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奈与不甘演绎得入木三分。
禳星失败后,诸葛亮强撑病榻,召来姜维、杨仪、费祎等心腹,安排“身后三事”,此为“托孤”情节的延伸,不同于史书中的政治托孤,豫剧更侧重于“精神传承”:诸葛亮先取出平生所著《兵法二十四篇》,交予姜维,嘱其“继我遗志,北伐中原”;再嘱杨仪、费祎“和睦朝堂,辅佐幼主”,言语间既有对蜀汉基业的忧虑,亦有对弟子后辈的期许,此处表演以“对白”与“内紧外松”的身段为主:演员虽卧榻之上,却仍挺直腰背,眼神如炬,当提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时,声线微颤却字字铿锵,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魂刻入骨血,尤其当后主刘禅派使者前来探病,诸葛亮强撑起身,面北而拜,唱“臣安敢不竭股肱,效死忠贞”,一句“臣今当去矣,陛下善保龙体”,泪洒衣襟,将君臣情谊与家国大义交织的复杂情感推向高潮。
秋风五丈原的最后一幕,是“归天”的悲怆,诸葛亮命人抬至军营中军帐,面西而卧,手握羽扇,眼神望向成都方向,营外风声更紧,帐内烛火摇曳,姜维等将领环榻跪泣,诸葛亮缓缓睁开双眼,唱“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生心血付东流”,声音渐弱却清晰,最终羽滑落,闭目而逝,享年五十四岁,豫剧在此处以“静”衬“悲”:全场演员定格跪姿,无一声哭喊,唯有低沉的“堂鼓”声由缓至急,再戛然而止,随后响起凄婉的唢呐曲,象征秋风呜咽、天地同悲,当杨仪发出“丞相归天矣”的哭喊时,众将齐声痛哭,声震营帐,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恨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为更直观呈现下集核心情节与艺术特色,特整理如下:
| 主要场次 | 情节要点 | 豫剧表演特色 |
|---|---|---|
| 五丈原禳星 | 诸葛亮设坛祈寿,魏延误灭七星灯 | “慢二八板”转“快二八板”唱腔,太极步与七星剑法结合,面部表情由坚定到绝望 |
| 病榻托事 | 传授兵法、安排朝政、嘱托后主 | 卧姿身段保持挺拔,对白沉稳有力,眼神传递忧虑与期许 |
| 面西归天 | 望成都而卧,羽扇滑落,溘然长逝 | 静默定格与唢呐烘托结合,哭腔由压抑到爆发,凸显悲壮氛围 |
该剧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跌宕起伏的剧情,更在于豫剧艺术对人物内心的深度挖掘:诸葛亮并非“神人”,而是一个会病痛、有遗憾、却始终以家国为先的凡人;唱腔的“抑扬顿挫”、身段的“虚实结合”,让“忠”“智”“悲”的形象立体可感,让观众在百年后仍能透过舞台,触摸到那个“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赤子灵魂。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豫剧《诸葛亮归天》中,“七星灯”被灭的情节有何象征意义?
解答:“七星灯”是剧中诸葛亮禳星续寿的核心道具,象征其生命与天命的连接,灯灭既暗示“天命不可违”,也暗喻诸葛亮北伐大业的终结——如同七星灯的熄灭,蜀汉“兴复汉室”的希望也随之破灭,魏延的“莽撞闯入”与“无心之过”,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强化了“人谋难胜天意”的悲剧色彩,让观众对诸葛亮的“无力感”产生深刻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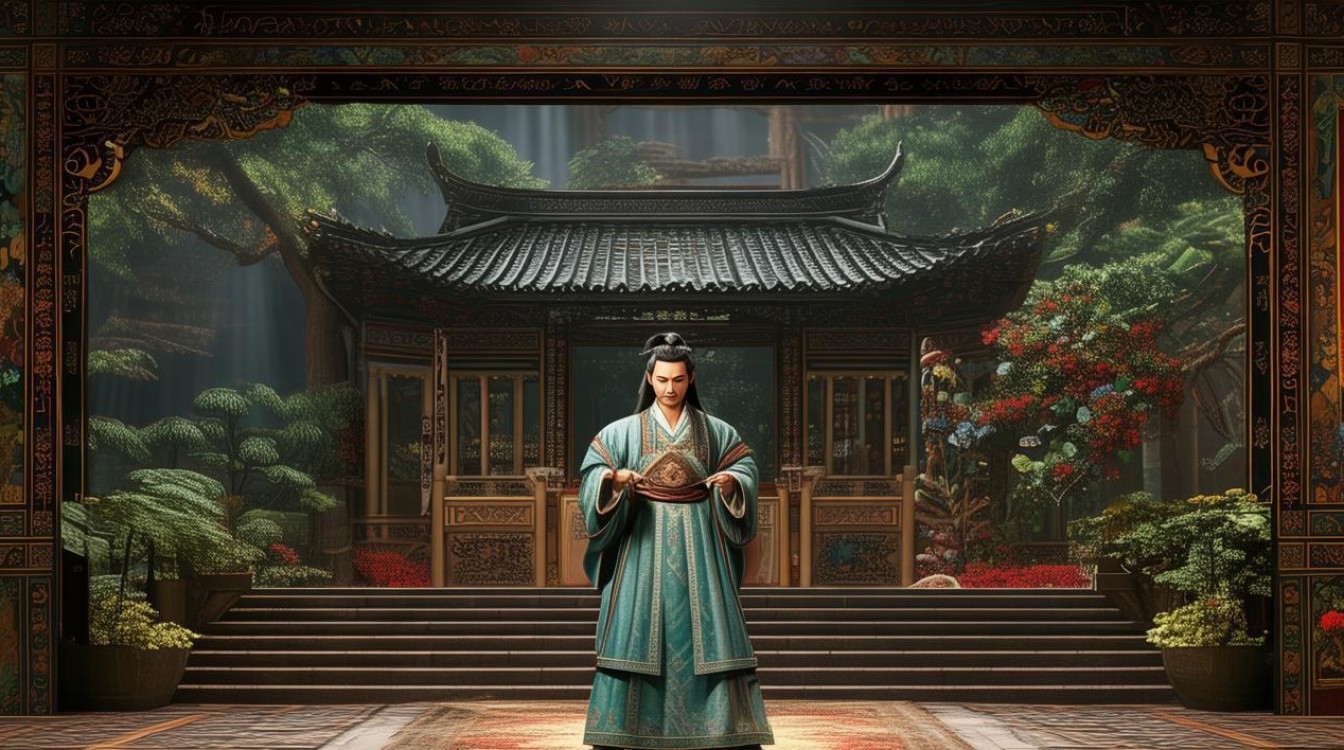
问题2:诸葛亮归天时,豫剧演员为何采用“面西而卧”的表演设计?
解答:“面西而卧”是豫剧对历史细节的艺术化处理: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而汉都洛阳位于蜀地之西,面西而卧象征其“心系中原、死不瞑目”的遗志,西方向来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终结”(如“日薄西山”),这一动作既贴合人物心境,又通过舞台方位的象征意义,强化了“英雄末路”的悲怆感,无需言语,便能让观众感受到其未竟事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