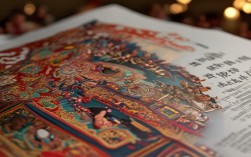京剧作为中国国粹,其音乐体系丰富多元,曲牌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塑造人物、渲染氛围、推动情节的功能,在众多京剧曲牌中,由笛子主奏的“汉东山”以其独特的旋律韵味和广泛的适用性,成为文场伴奏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本文将从历史渊源、音乐构成、结构解析、演奏技巧、运用场景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对京剧笛子曲牌“汉东山”进行详细阐述。

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汉东山”属于京剧“吹打曲牌”中的细乐类,其雏形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民间俗曲与戏曲声腔,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记载,该曲牌在清代中叶已逐渐融入京剧前身“徽班”的音乐体系,可能吸收了昆曲“东山西调”的旋律元素,并结合北方民间吹打乐的节奏特点,最终形成京剧化的曲牌形态,其名称“汉东山”虽无明确史料记载其典故,但从“汉”字的文化寓意(如汉韵、汉风)及“东山”的意象(如归隐、闲适)推测,可能与表现传统文人雅士或历史人物的特定情境相关,在京剧发展过程中,汉东山因旋律简洁、适配性强,被文场乐师(以笛子、笙、胡琴等为主)广泛采用,成为区别于“急急风”“夜深沉”等武场或特定情绪曲牌的“通用型”文牌。
音乐构成与旋律特点
汉东山的音乐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多采用G调或D调(笛子筒音作5或2),调式上以宫调式为主,偶尔穿插羽调式的色彩变化,形成“端庄中见灵动”的听觉效果,其旋律线条平缓流畅,以级进音程为主,辅以四度、五度的跳进,无明显的大起大落,符合“中正平和”的审美传统,节奏方面,以4/4拍为主,速度多为中速(♩=80-100),偶尔在段落结尾处渐慢,形成“起—承—转—合”的呼吸感。
从音程关系看,汉东山的核心音型常以“sol-la-do-re”或“re-mi-sol-la”为基础,通过重复、模进等手法发展,例如开篇常用“sol sol la | do re |”的短句,随后以“sol la do | re do |”呼应,既保持旋律的连贯性,又通过重复强化记忆点,装饰音的运用是其特色之一,以单倚音、复倚音为主,尤其在长音(如do、sol)前加入小二度或大三度的倚音,模拟戏曲唱腔中的“润腔”效果,增强旋律的韵味,笛子的“气滑音”“指滑音”技巧在演奏中被频繁使用,使旋律如“行云流水”,避免机械化的音符堆砌。
结构解析:程式化框架中的灵活变奏
汉东山作为京剧曲牌,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框架,但在实际运用中可根据剧情需要灵活调整,以下是其典型结构的分段解析(以G调笛子演奏为例,共32小节):
| 段落 | 小节数 | 速度 | 节拍 | 情绪/功能 | 旋律特点 |
|---|---|---|---|---|---|
| 引子 | 1-4 | 散板 | 自由 | 铺垫氛围,引入情境 | 以长音“sol”起奏,辅以下滑音,营造“远山如黛”的意境 |
| 主体A | 5-12 | 中速 | 4/4 | 叙述性段落,平稳推进 | 以“sol la do re |
| 主体B | 13-20 | 中速稍快 | 4/4 | 情绪递进,略有起伏 | 加入四度跳进“do sol la |
| 连接段 | 21-24 | 渐慢 | 4/4 | 过渡与准备 | 以“re mi fa |
| 高潮C | 25-28 | 稍快 | 4/4 | 情绪释放,点睛之笔 | 重复“sol sol la |
| 尾声 | 29-32 | 渐慢 | 散板 | 收束情绪,回归宁静 | 以“sol mi re do |
这种“引子—主体—连接—高潮—尾声”的结构,既符合传统曲牌的程式化要求,又通过主体段落的重复与变奏(如主体B对主体A的音高调整)实现“统一中求变化”,在实际演出中,乐师可根据剧情需要删减段落(如省略引子或缩短高潮),或通过加花演奏(在音符间加入短小的装饰音)丰富层次,体现京剧音乐“死腔活唱”的灵活性。
演奏技巧与笛子表现
笛子作为汉东山的主奏乐器,其演奏技巧直接决定曲牌的韵味表现,气息控制是关键:引子部分的长音需采用“缓吹法”,气息深沉而稳定,配合下滑音模拟“叹息感”;高潮段的吐音则需使用“单吐”或“双吐”,颗粒清晰,突出节奏的推进力,手指技巧方面,“颤音”(在长音上快速开闭按音孔)和“打音”(重音前的短促装饰音)的运用能增强旋律的生动性,例如主体A中的“la”音前加入打音,可避免旋律的平直。

笛子的“循环换气法”在长乐句中尤为重要,如主体B的“do re mi fa sol fa mi re”一句,需通过鼻腔吸气与口腔呼气的交替,实现音符的连贯不断,保证旋律的流畅性,音色处理上,汉东山要求笛子音色“清亮而不浮躁”,多用“平吹”(气息与笛孔垂直),避免过多的气息冲击导致音色过噪,体现“雅乐”的审美特质。
京剧中的运用场景与功能
汉东山因其“中性化”的音乐性格,在京剧中的运用场景极为广泛,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文人物境的渲染
多用于表现文人雅士、官员贵族的从容姿态或闲适场景,群英会》中周瑜与诸葛亮对弈时,后台笛子吹奏汉东山,旋律平缓中暗含机锋,既烘托了棋局紧张的“文戏武唱”,又通过音乐的“静”反衬人物内心的“动”。《贵妃醉酒》中杨贵妃赏花时的背景音乐,则以汉东山的高潮段配合水袖动作,表现其雍容华贵与内心的孤寂。
场景转换的过渡
在京剧“场戏转换”中,汉东山常作为“过场曲牌”,衔接不同时空的剧情,空城计》中诸葛亮城楼抚琴后,转至司马懿大军压境时,通过汉东山从散板到中速的过渡,既完成场景切换,又通过音乐的“舒缓”暗示诸葛亮的镇定自若。
武戏中的“文武配合”
在部分武戏中,汉东山与武场锣鼓结合,形成“文武相济”的效果,长坂坡》赵云救主时,笛子吹奏汉东山的高潮段,配合急急风的锣鼓点,旋律的“长线条”与锣鼓的“短节奏”形成对比,既突出赵云的英勇,又避免武戏的“喧闹过度”。
艺术特色与当代价值
汉东山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三性”:一是程式性,其结构、调式、旋律框架符合京剧曲牌的规范,便于乐师掌握与传承;二是适应性,通过速度、力度、装饰音的调整,可适配喜悦、从容、含蓄等多种情绪,突破单一曲牌的局限性;三是韵味性,笛子的滑音、颤音等技巧与戏曲唱腔的“润腔”相通,使音乐具有“唱奏一体”的感染力。

在当代京剧创作中,汉东山仍被广泛运用,甚至成为“新编京剧”的“音乐符号”,曹操与杨修》中,汉东山被融入现代和声元素,加入钢琴伴奏,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体现人物内心的复杂矛盾,汉东山也被纳入中小学京剧普及教育,通过其简洁的旋律让学生感受戏曲音乐的魅力,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相关问答FAQs
Q1:汉东山与京剧常用笛子曲牌《夜深沉》在音乐风格和运用场景上有何区别?
A:汉东山与《夜深沉》均以笛子主奏,但风格迥异。《夜深沉》源自昆曲《思凡》,旋律低沉婉转,节奏多变(散板至流水板),多用于表现悲壮、压抑或激烈的情绪,如《霸王别姬》中虞姬舞剑、《击鼓骂曹》中祢衡击鼓的场景;而汉东山则明快流畅,节奏平稳,以中速为主,多表现文雅、从容或过渡性情境,如文人行路、宴饮或场景转换,两者在情绪色彩与功能定位上形成“文武”“悲喜”的对比。
Q2:现代京剧创作中,汉东山曲牌是否进行了创新?如有,体现在哪些方面?
A:是的,现代京剧创作中对汉东山进行了多维度创新,一是配器创新,如在《红灯记》中,将汉东山与西皮流水板融合,加入电子合成器伴奏,笛子与弦乐、打击乐形成“立体化”音响;二是旋律创新,如《骆驼祥子》中,在汉东山主体段加入降七音、降三音等变化音,表现老北京城的时代沧桑感;三是结构创新,如《觉醒年代》中,打破传统“引子—主体”结构,以汉东山的核心音型为动机,通过变奏、复调手法发展成贯穿全剧的“主题音乐”,强化人物形象的统一性,这些创新既保留了汉东山“以简驭繁”的传统基因,又赋予其当代审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