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向来以“高台教化”为己任,将忠孝节义、家国大义融入唱念做打,天职”二字更是无数剧目的精神内核,所谓“天职”,既是天地赋予的本分,也是人心向善的坚守,在戏曲舞台上,它化作程婴的舍生取义、包拯的铁面无私、薛湘灵的扶危济困,于悲欢离合中演绎出中国人最质朴的价值观,近日重温经典戏曲剧目,对“天职”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悟——它不仅是古人行为的准则,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灯塔,照亮当代人前行的路。

传统戏曲中的“天职”根植于儒家伦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脉络,在不同身份角色中呈现出多元样态,士大夫以“忠”为天职,如《赵氏孤儿》中程婴,为存忠良之后,不惜献出亲子,背负骂名十五年,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决绝,正是对“忠”字的极致诠释;执法者以“公”为天职,《铡美案》里包拯面对陈世美的权势诱惑,不畏皇亲国戚,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铡刀落下的是法理,更是对“公”字的守护;普通人则以“善”为天职,《锁麟囊》的薛湘灵在富贵时赠囊救人,落难时受囊知恩,用一囊之诺诠释了“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朴素天职,这些角色虽身份不同,却共同指向“各安其分,各尽其责”的伦理追求。
| 剧目 | 人物 | 天职内涵 | 艺术表现 |
|---|---|---|---|
| 《赵氏孤儿》 | 程婴 | 义士之忠(存孤) | 舍子救孤、十五年忍辱负重 |
| 《铡美案》 | 包拯 | 执法之公(护法) | 铡美陈、不畏权势、脸谱象征刚正 |
| 《锁麟囊》 | 薛湘灵 | 人之善(守信) | 赠囊、受囊、举手投足显仁厚 |
| 《打金枝》 | 郭子仪/李君 | 君臣/夫妻之责(和) | 劝君、负荆请罪、唱腔化解矛盾 |
戏曲中的“天职”往往不是坦途,而是充满牺牲与抉择的荆棘路,程婴的“忠”需以亲子性命为代价,包拯的“公”要对抗皇权与人情的双重压力,薛湘灵的“善”在落难时更显珍贵,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让天职的坚守更具悲剧张力,却也因悲剧而愈发崇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戏曲通过展现人物在天职与私欲间的挣扎,让观众在共情中领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重量——这种重量,正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坠的脊梁。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天职”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是单一的家国大义,而是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是医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是科研工作者“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戏曲中的天职观告诉我们,“天职”不分大小,只要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内心的责任,便值得倾尽全力,当我们为程婴落泪,为包拯叫好,为薛湘灵动容时,实则是在唤醒内心深处对“责任”的敬畏——这份敬畏,恰是构建现代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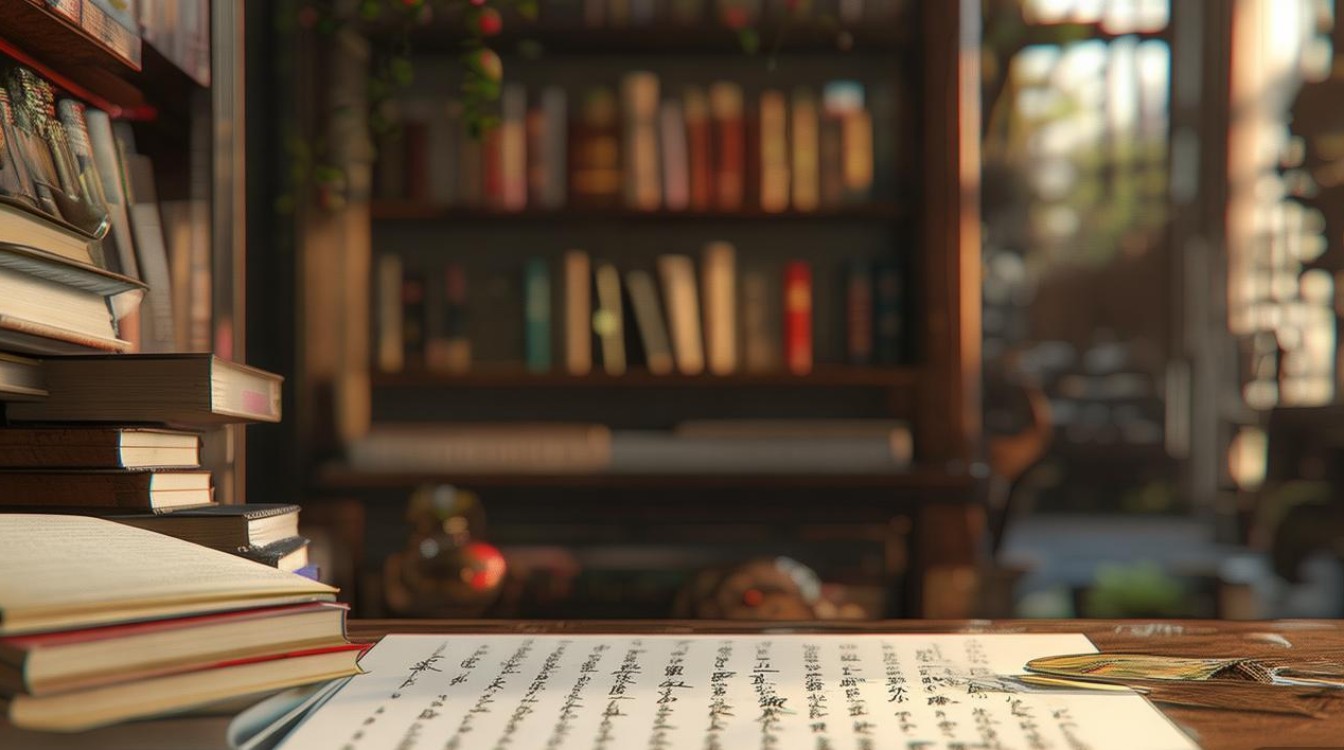
戏曲落幕,余音绕梁。“天职”二字,从古至今,从舞台到生活,始终是衡量人性光辉的标尺,它教会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书写不凡,在个人的选择中亦可成就大义,愿我们都能从戏曲的天职故事中汲取力量,以责任为笔,以担当为墨,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
FAQs
问题1:戏曲中的“天职”观念与现代职业伦理有何异同?
解答:二者的核心相同点在于对“责任”的强调,都要求从业者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不同点在于,传统戏曲的“天职”多与儒家伦理绑定,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如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且常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而现代职业伦理更强调平等、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注重在保障个体权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价值,例如现代医生既要救死扶伤,也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传统戏曲中“义以为上”的精神内核,仍是现代职业伦理的重要文化根基。
问题2:为什么传统戏曲中“天职”主题往往伴随着悲剧色彩?
解答:这与中国传统悲剧的美学特质有关,戏曲通过“天职”与人性欲望的冲突制造戏剧张力,如程婴的“忠”与“父爱”冲突,包拯的“公”与“私情”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以主人公的牺牲、受难为结局,符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悲剧性更能凸显“天职”的崇高感——正是因为坚守天职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让观众对其产生敬畏与共鸣,从而实现“高台教化”的目的,这种“以悲写德”的艺术手法,让“天职”观念更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