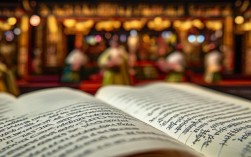苏武牧羊的故事作为中国历史上忠贞不屈的象征,历经千年传颂不衰,而京剧《苏武牧羊》则通过这门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让这一经典形象在舞台上焕发新生,冯志孝以其深厚的裘派功底与细腻的人物塑造,成为诠释苏武的代表性演员,其表演不仅传承了传统京剧的艺术精髓,更赋予了角色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苏武传》,其“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的细节,成为气节的千古注脚,京剧《苏武牧羊》在历史原型基础上,进行了戏剧化的提炼与加工,将苏武的十九年牧羊生涯浓缩为“被困北海”“劝降交锋”“持节归汉”等关键情节,通过唱、念、做、舞的综合呈现,突出其面对威逼利诱时的坚定与孤独,剧中,苏武的核心唱段如“叹苏武身困在沙漠荒外”“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载”等,以二黄、西皮板式为依托,既抒发了人物内心的悲愤与思念,也彰显了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风骨。
冯志孝作为裘派老生的杰出传人,自幼受裘盛戎先生亲授,深得裘派“唱腔刚劲挺拔,念白铿锵有力,表演质朴深沉”的艺术真谛,在《苏武牧羊》中,他将裘派的“唱念做打”与苏武的人物特质完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唱腔上,冯志孝嗓音高亢而醇厚,擅长运用“脑后音”“擞音”等技巧,如“叹苏武”唱段中,“身困在沙漠荒外”的“荒”字,以苍劲的下滑音表现环境的险恶;“手持着节杖”的“节”字,用顿音突出节杖的分量,拖腔“十九载”的起伏处理,既传递了时间的漫长,又暗含了内心的坚守,念白方面,他结合韵白的韵律美与京白的口语化,如与匈奴单于、李陵的对话中,或正气凛然,或痛陈心迹,字字句句皆透出苏武的刚直与赤诚,身段表演上,冯志孝注重细节刻画:持节杖时的稳健步伐,抚摸节旄时的颤抖手指,望向南方时的凝眼神态,都将苏武的孤独与思念具象化,让观众在程式化的动作中感受到真实的人物情感。
以下为京剧《苏武牧羊》主要情节与冯志孝表演处理的对应分析:

| 情节段落 | 冯志孝表演处理 | 艺术效果 |
|---|---|---|
| 北海被困 | 二黄导板起唱,身段蜷缩,眼神望向远方,抚摸节旄时手指微颤 | 表现苏武身处绝境的悲愤与对故国的思念,苍凉的唱腔与压抑的身段形成强烈感染力 |
| 劝降交锋 | 西皮流水板驳斥匈奴,甩袖、顿步配合铿锵念白,眼神坚定如炬 | 以快节奏唱腔与利落身段展现苏武的不屈,驳斥时的声调起伏凸显其“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
| 持节归汉 | 二黄散板转高亢,节杖挥舞,眼神明亮含泪,步履由缓到急 | 通过唱腔的激昂与身段的舒展,传递苏武归汉时的激动与忠贞,将情绪推向高潮 |
冯志孝的苏武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在于其精湛的技艺,更在于他对人物精神内核的深刻把握,他将苏武的“忠”与“贞”转化为可感的舞台形象,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程式美,又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让历史人物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演苏武,要演出‘节’的分量,更要演出‘人’的温度——他不是神,而是一个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的普通人。”这种“神形兼备”的表演,让《苏武牧羊》成为裘派艺术传承中的经典剧目,也让苏武的精神通过京剧舞台持续闪耀。
FAQs
问题1:冯志孝在《苏武牧羊》中如何通过唱腔表现苏武的内心变化?
解答:冯志孝根据剧情发展灵活运用唱腔板式与技巧,初陷北海时,以二黄慢板、导板为主,唱腔低沉苍凉,通过下滑音、擞音表现悲愤与孤独;面对劝降时,转西皮流水板,节奏加快,音调铿锵,用顿音与甩腔凸显不降的决心;归汉时,以二黄散板转高亢唱腔,拖腔饱满,音程起伏大,传递喜悦与忠贞,不同板式的转换与技巧的运用,精准勾勒出苏武从悲愤到坚定,再到激动的情感轨迹。
问题2:京剧《苏武牧羊》与其他剧种(如越剧、黄梅戏)的同名剧目相比,有哪些独特艺术特点?
解答:京剧《苏武牧羊》的独特性在于其“程式化”与“写意性”的融合,一是唱腔以西皮、二黄为核心,板式丰富(如导板、回龙、流水等),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区别于越剧的柔美抒情(如尺调腔)与黄梅戏的质朴生活化;二是身段表演高度程式化,如“马鞭”代跋涉、“髯口功”显情绪,通过虚拟动作展现环境与心理,更具京剧的“意象美”;三是念白结合韵白与京白,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增强舞台感染力,使苏武的形象更具历史厚重感与舞台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