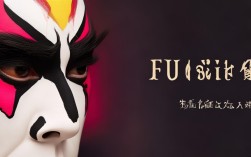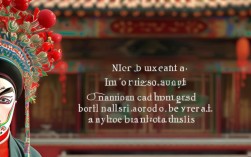中国戏曲的写法是融合文学、音乐、表演、美术等多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创作体系,其核心在于“以歌舞演故事”,既遵循规范化的程式,又包含灵活即兴的创造,最终实现“情、景、人、事”的舞台化呈现,这种写法并非单一的文字创作,而是贯穿于剧本文学、舞台表演、观众接受的全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剧本文学的写法:结构、语言与人物塑造
戏曲剧本是戏曲写法的文学基础,其创作需兼顾“可读性”与“可演性”,既要文字优美,又要为表演留出空间。
结构:线性叙事与程式化框架
传统戏曲剧本多采用“线性叙事”结构,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为基本脉络,常用“楔子”(开场交代背景)、“出”(或“折”,剧情段落)、“尾声”(收束归纳)的形式组织全剧,例如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结构(《窦娥冤》),楔子交代窦天章卖女,第一折窦娥嫁蔡婆,第二折张驴儿逼婚,第三折窦娥被冤斩首,第四折窦天章昭雪雪冤,情节紧凑,冲突集中,明清传奇则篇幅更长,如《牡丹亭》五十五出,以“梦—情—死—生”为主线,通过“游园惊梦”“幽誓”“闹殇”“圆驾”等出目,层层递进展现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
结构上还讲究“起承转合”的节奏把控:开端“起”要简明,迅速引入人物和矛盾(如《西厢记》第一张“佛殿奇逢”介绍张生与崔莺莺相遇);发展“承”要铺陈,通过细节丰富人物性格(如《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盟誓);高潮“转”要激烈,矛盾冲突达到顶点(如《赵氏孤儿》第四折“搜孤救孤”程婴与屠岸贾的正面冲突);结局“合”要圆满,符合“大团圆”的传统审美(如《白蛇传》水漫金山后,白素贞被压雷峰塔,最终儿子中状元救母)。
语言:曲白相生,雅俗共赏
戏曲剧本由“曲”(唱词)和“白”(宾白)两部分构成,语言风格因剧种、行当而异,但总体追求“文采”与“通俗”的统一。
-
曲词:讲究格律与意境,需配合曲牌或板式演唱,昆曲用“曲牌体”,每支曲牌有固定字数、平仄、押韵,如《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通过“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的对比,营造凄美意境;京剧用“板腔体”,以“西皮”“二黄”为基础,通过“慢板”“原板”“流水板”等板式变化调节节奏,如《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南梆子唱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唱腔舒缓,表现悲凉,曲词善用修辞,比喻(如《牡丹亭》“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对偶(如《桃花扇》“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用典(如《长生殿》“此恨绵绵无绝期”化用白居易诗句),既增强文采,又深化情感。
-
宾白:分为“韵白”(韵律化念白,如京白、韵白)和“散白”(口语化念白,如方言白、市井白),韵白讲究抑扬顿挫,如《铡美案》中包拯的念白“驸马近前,端详端详”,字正腔圆,凸显刚正;散白贴近生活,如《秋江》中陈妙常的念白“老艄公,船快些摇呀呀”,活泼生动,体现少女急切,宾白的作用是推动剧情、交代背景、塑造人物,如《西厢记》红娘的念白“张先生,你读书人,礼之用,和为贵”,既推动张生与崔莺莺的感情发展,又展现红娘的机智善良。

人物塑造:行当分类与符号化表达
戏曲人物通过“行当”分类(生、旦、净、丑),每个行当有固定的表演程式和语言风格,形成“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
- 生:男性角色,分老生(中年以上男性,如诸葛亮)、小生(青年男性,如张生)、武生(武将,如赵云),老生的唱腔苍劲,念白沉稳,如《空城计》诸葛亮“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段,表现智勇双全;小生的唱腔清亮,念白文雅,如《西厢记》张生“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的念白,体现书生气。
- 旦:女性角色,分青衣(端庄女性,如王宝钏)、花旦(活泼少女,如红娘)、武旦(女将,如穆桂英),青衣的唱腔婉转,身段端庄,如《三击掌》王宝钏“老爹爹请上受儿拜”的唱段,表现刚烈;花旦的念白俏皮,身段灵动,如《春草闯堂》春草“你既是公子,怎的这般狼狈”的念白,体现机敏。
- 净:性格鲜明的男性,分铜锤花脸(正直,如包拯)、架子花脸(奸诈,如曹操),净角唱腔粗犷,念白洪亮,脸谱夸张(如包拯的黑脸、曹操的白脸),通过色彩和图案象征性格(黑脸表忠义,白脸表奸诈)。
- 丑:喜剧角色,分文丑(文人、小吏,如崇公道)、武丑(武艺高强的丑角,如时迁),丑角念白口语化,动作滑稽,常插科打诨,调节气氛,如《女起解》崇公道“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念白,幽默风趣,体现底层小人物的市井气息。
表演与剧本的程式化互动:写法的“活态呈现”
戏曲的写法不仅存在于文字,更通过“程式化表演”在舞台上“复活”,程式是戏曲表演的“语法”,包括唱、念、做、打四大基本功,与剧本内容紧密结合,形成“演什么,怎么演”的规范。
做功:身段与动作的虚拟写法
戏曲表演不追求写实,而是通过“虚拟动作”表现生活场景,这是写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开门”:演员用手势模拟推门,配合眼神和台步,观众能理解是“开门”,无需真实门;“骑马”:演员手持马鞭,跑圆场(台步),观众能想象是“骑马”;“上楼”:演员抬腿、转身,配合眼神仰视,观众能感知是“上楼”,这些虚拟动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夸张化”和“美化”形成程式,如《拾玉镯》中孙玉姣拾镯的动作,通过“指、捏、看、笑”等一系列身段,表现少女的羞涩与喜悦,既细腻又传神。
打功:武打的程式化设计
武打是戏曲冲突的重要手段,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如“起霸”(武将出征前的整装,包括整冠、束带、抬腿、亮相等动作)、“走边”(夜间潜行的动作,包括蹑足、观望、翻跃等)、“开打”(双方对打,包括“对枪”“对刀”“翻跟头”等),长坂坡》中赵云“七进七出”的武打,通过“单枪对群敌”“翻越城墙”等程式,表现赵云的勇猛;三岔口》的“打”则在黑暗中进行,演员通过摸爬滚打、躲闪攻击的动作,表现“夜战”的紧张,全凭程式让观众理解场景。
唱念做打的融合:剧本与表演的“共生”
剧本中的唱词和念白是表演的“蓝本”,而唱念做打则是“蓝本”的“演绎”,霸王别姬》中虞姬的“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唱段,剧本只写唱词,演员通过“慢板”唱腔(唱)、低头凝视的眼神(念)、水袖轻拂的动作(做)、配合鼓点的节奏(打),表现虞姬对霸王的担忧与无奈,使文字转化为有情感的舞台形象,程式化表演允许“即兴发挥”,如在折子戏中,演员可根据现场气氛调整念白的节奏或身段的幅度,但需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逻辑,这种“死中求活”的写法,使戏曲既有规范又有生命力。
不同剧种的写法差异:地域文化的艺术投射
中国戏曲剧种众多,每个剧种因地域文化、语言、音乐的不同,形成独特的写法风格,以下以昆曲、京剧、川剧为例对比:

| 剧种 | 代表剧目 | 结构特点 | 语言风格 | 音乐体系 | 表演程式特点 |
|---|---|---|---|---|---|
| 昆曲 | 《牡丹亭》《长生殿》 | 长篇本戏,分“出”,每出有固定套曲,结构严谨 | 文雅,多典故,辞藻华丽(如“袅晴丝吹来闲庭院”) | 曲牌体,“水磨腔”,唱腔细腻婉转 | 舞台写意,身段“一招一式”规范,如杜丽娘“游园”的“花锄”“花篮”动作 |
| 京剧 | 《霸王别姬》《铡美案》 | 折子戏为主,结构灵活,冲突集中 | 通俗化,京白口语化(如《四郎探母》“叫小番”的念白) | 板腔体,以西皮(明快)、二黄(深沉)为基础,板式丰富 | “唱念做打”并重,脸谱夸张(如关羽红脸、张飞黑脸),身段“虚拟化”强(如“趟马”表现骑马) |
| 川剧 | 《白蛇传·金山寺》《变脸》 | “帮打唱”结合,高腔为主,结构自由,加入方言和插科打诨 | 方言化(四川话),幽默风趣(如《秋江》陈妙常“老艄公,船快些摇”的念白) | “五腔共和”(高腔、胡琴、昆腔、弹戏、灯调),高腔徒歌而舞 | “变脸”“吐火”绝活,写法“夸张性”强(如《金山寺》法海变脸表现神通) |
传统与现代的写法演变:从继承到创新
传统戏曲写法强调“守格”,即遵循程式和规范,如明清传奇的“四部结构”、京剧的“西皮二黄”板式,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代戏曲创作在“守格”基础上“破格”,赋予戏曲写法新的内涵。
保留核心程式,但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的“趟马”程式,不再表现传统武将,而是通过演员的台步和身段,表现人力车夫的艰辛,程式成为表现当代生活的“符号”;创新叙事方式,借鉴话剧、影视的技巧,茶馆》采用“三幕式”结构,通过裕泰茶馆的三个历史片段(清末、民国、抗战后),展现社会变迁,打破了传统戏曲“一线到底”的叙事;《尘埃落定》根据阿来小说改编,用藏语唱词结合藏族舞蹈,将民族元素融入戏曲写法,拓展了戏曲的表现边界。
现代写法还注重“观众意识”,通过主题的当代化引发共鸣,焦裕禄》通过戏曲写法表现干部的奉献精神,用“唱腔”表现焦裕禄的内心挣扎(如“风雪夜归人”唱段),用“做功”表现他与群众的互动(如“访贫问苦”的身段),使传统戏曲与现代观众的情感需求对接。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戏曲剧本的唱词如何通过格律和修辞体现人物性格?
解答:戏曲唱词的格律(如昆曲的曲牌体、京剧的板腔体)和修辞(比喻、对偶、用典)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昆曲《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用“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的对比,结合“皂罗袍”曲牌的婉转唱腔,表现大家闺秀的敏感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通过“西皮流水板”的明快节奏和排比修辞,展现英雄人物的豪迈气概,净角的唱词多用粗犷的“花脸腔”,如《铡美案》中包拯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唱腔高亢,凸显刚正不阿;丑角的唱词则口语化、诙谐,如《女起解》中崇公道的“苏三离了洪洞县”,语言通俗,体现市井气息。
问题2:现代戏曲创作中,如何平衡传统写法的程式化与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解答:现代戏曲创作通过“程式化内容的现代化转化”和“叙事方式的创新”来平衡传统与当代审美,保留核心程式(如唱腔、身段、脸谱),但赋予其新的内涵。《新龙门客栈》中“打斗”程式融入武侠片的“快节奏”,通过翻跟头、对枪等动作表现江湖恩怨,程式成为“武侠美学”的载体;创新叙事结构,借鉴话剧的“线性叙事”和影视的“蒙太奇”。《青春之歌》采用多幕式结构,通过“读书—被捕—斗争—成长”四个场景,展现知识青年的觉醒,节奏更符合现代观众的观影习惯,在语言上,传统戏曲的文雅唱词可适当口语化(如《暗恋桃花源》融入现代词汇),但保留韵律美;在主题上,关注当代社会议题(如《生命如歌》表现抗疫精神),使传统戏曲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守正创新”的写法,既保留了戏曲的艺术精髓,又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