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发源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其前身是昆山腔,经顾坚等民间艺人整理,至明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以昆山腔为基础,吸收海盐腔、余姚腔的优点,革新唱腔,创“水磨调”——其唱腔细腻婉转,如清泉击石,转音若丝,讲究“字清、腔纯、板正”,使昆山腔从地方声腔发展为雅致的戏曲形式,隆庆年间,剧作家梁辰鱼用新腔创作《浣纱记》,首次将昆曲搬上舞台,标志昆曲的成熟,此后,昆曲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明清两代主流剧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皆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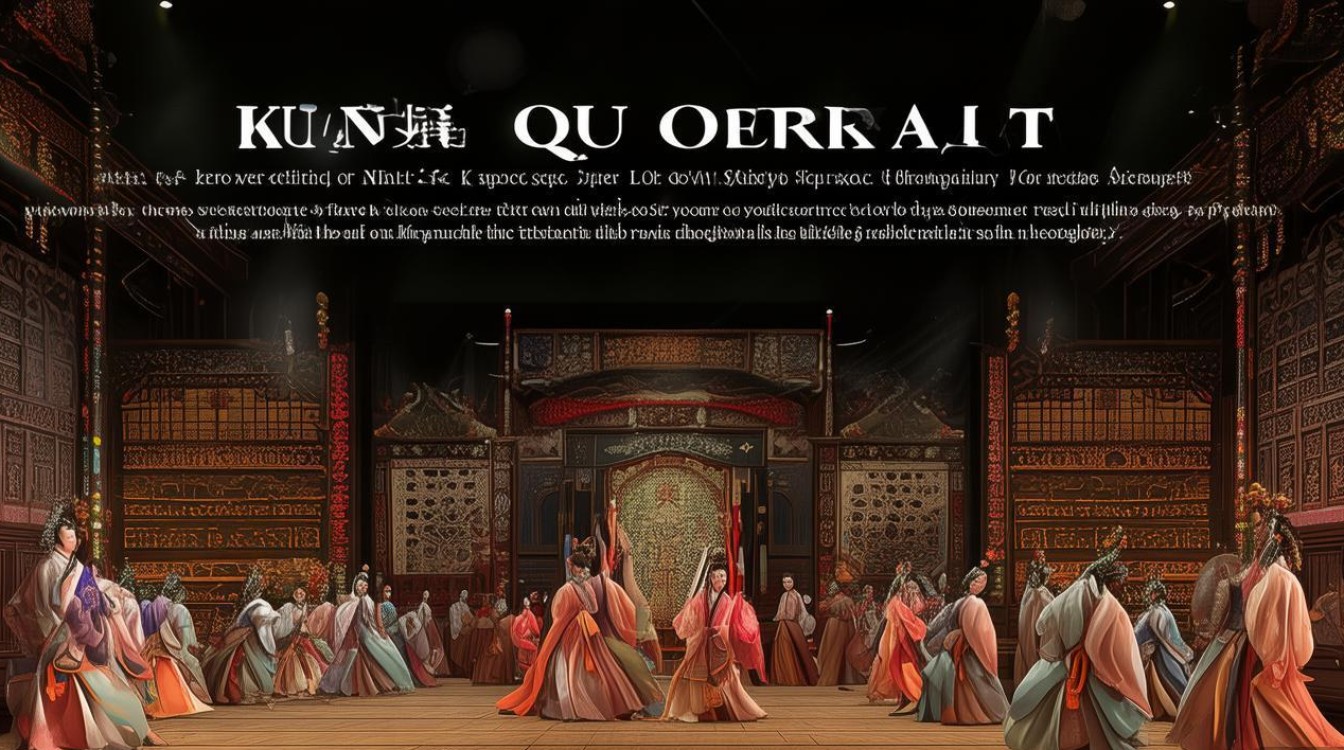
昆曲的艺术魅力体现在其独特的“唱、念、做、打”综合体系中,尤以“唱”为核心,其唱腔以曲牌体为结构,每个曲牌有固定格律与旋律,如《皂罗袍》《山坡羊》等,通过联套组成完整唱段,演唱时讲究“依字行腔”,即根据字音的平仄、阴阳调整旋律,使字正腔圆,情感表达细腻入微,牡丹亭·惊梦》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通过高低起伏的旋律,将杜丽娘对春光的赞叹与青春易逝的伤感融为一体,余韵悠长。
表演上,昆曲追求“载歌载舞”,动作程式化且极具美感,旦角的“兰花指”、生角的“云手”、净角的“亮相”等,皆有严格规范,每一个眼神、手势都蕴含特定情感,如《牡丹亭·寻梦》中杜丽娘的“游园”身段,通过轻移莲步、水袖翻飞,将少女的娇羞与对爱情的向往演绎得淋漓尽致,昆曲的“做功”强调“无动不舞”,即便是简单的开门、上楼,也被提炼为舞蹈化的动作,虚实结合,意境深远。
文学性是昆曲的另一大特质,其剧本多出自文人墨客之手,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文辞典雅,意境深远,这些作品不仅注重情节的曲折,更追求哲思的表达,如《牡丹亭》以“情”反“理”,歌颂人性解放;《长生殿》借帝妃爱情反思历史兴衰;《桃花扇》以离合之情写南明覆灭,被誉为“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剧本的文学性与音乐性高度统一,唱词如诗,便于抒情,也使昆曲超越单纯的娱乐,成为“雅部”艺术的代表。
昆曲的行当分工细致,各具特色,如下表所示:

| 行当 | 分类 | 代表角色 | 表演特点 |
|---|---|---|---|
| 生 | 老生、小生、武生 | 唐明皇(《长生殿》)、柳梦梅(《牡丹亭》) | 唱腔醇厚,身段儒雅,小生重“翎子功” |
| 旦 | 正旦、闺门旦、刺杀旦 | 杜丽娘(《牡丹亭》)、李香君(《桃花扇》) | 唱腔婉转,身段柔美,重“水袖功” |
| 净 | 大花脸、二花脸 | 钟馗(《嫁妹》) | 唱腔粗犷,脸谱鲜明,动作夸张 |
| 末 | 老生 | 侯方域(《桃花扇》) | 唱念苍劲,表演沉稳 |
| 丑 | 文丑、武丑 | 崇伯(《十五贯》) | 语言诙谐,动作滑稽,重“矮子功” |
昆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清代中后期,随着花部(地方戏)的兴起,昆曲逐渐衰落,演出市场萎缩,艺人流散,民国时期,昆曲更陷入“传人无几,剧目失传”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扶持,1956年浙江昆剧团改编演出《十五贯》,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让昆曲重获生机,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其文化价值得到世界认可,当代昆曲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也尝试创新,如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以现代审美重构经典,吸引年轻观众,为古老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如此,昆曲仍面临观众老龄化、传承人断层、市场化不足等挑战,如何在保护传统精髓的前提下实现活态传承,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昆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始终在戏曲史上熠熠生辉,成为世界艺术殿堂中的璀璨明珠。
FAQs
-
问:昆曲为什么被称为“百戏之祖”?
答: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其声腔、表演体系对后世众多剧种(如京剧、川剧、湘剧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京剧的形成就吸收了昆曲的曲牌、念白和身段技巧,昆曲的剧本创作、音乐理论和表演规范为后世戏曲提供了范式,具有“源头”地位,故称“百戏之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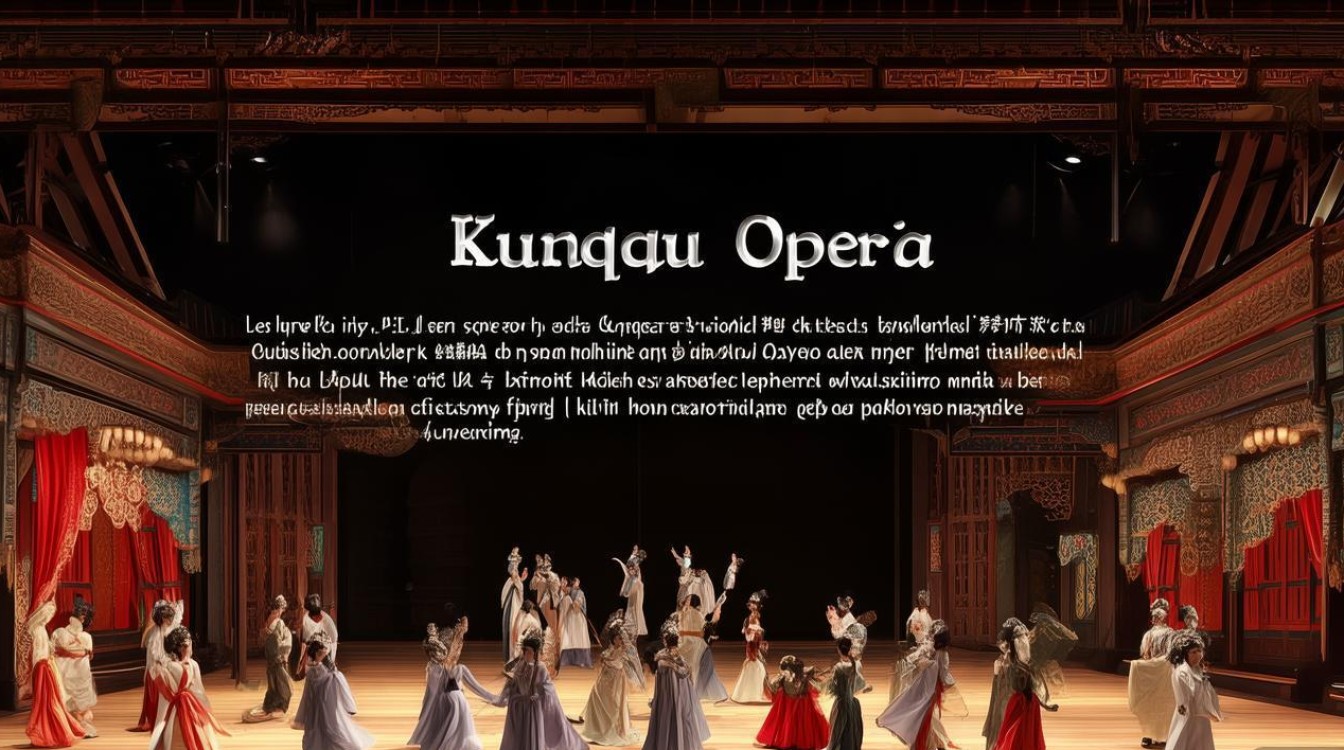
-
问:学习昆曲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功?
答:学习昆曲需掌握“唱、念、做、打”四大基本功,唱腔上要练好“水磨调”,掌握气息控制、发音吐字技巧;念白需区分韵白(戏曲化念白)和散白(生活化念白),做到字正腔圆;身段包括台步、手势、眼神、水袖等,需经长期训练形成程式化动作;武打则需练习毯子功(翻、跌、扑)和把子功(兵器对打),还需具备文学修养,理解剧本内涵,才能准确演绎人物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