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牟雅,这个名字在当代戏曲界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以其惊才绝艳的艺术天赋和对昆曲艺术的执着坚守,重新定义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戏曲的认知,他并非科班出身的“学院派”,却以惊人的悟性和对角色的深刻洞察,在昆曲的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经典形象;他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的风骨,又带着年轻人对创新的敏锐,让古老的“百戏之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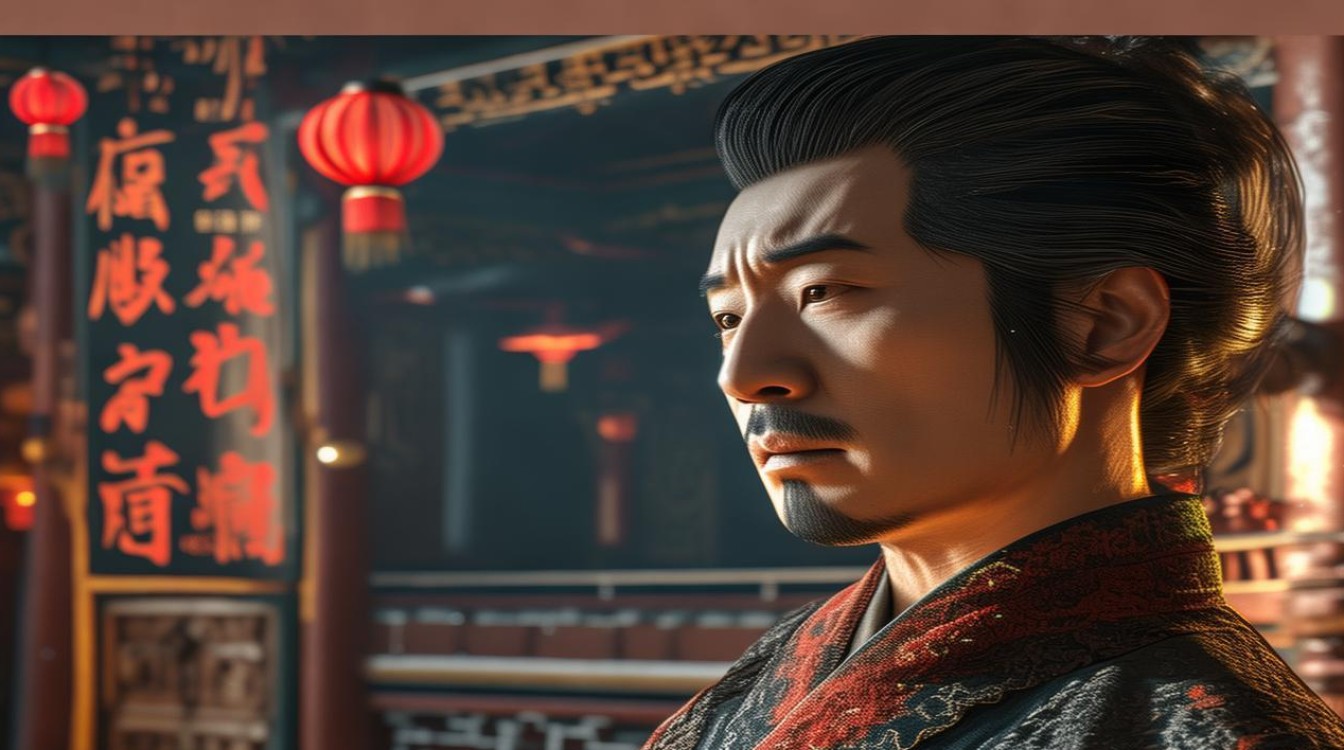
从“戏痴少年”到“昆曲新星”:天赋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1995年,李牟雅出生于江南一座水乡小镇,自小便浸润在吴侬软语的戏曲氛围中,他的祖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昆曲票友,常在家中哼唱《牡丹亭》的片段,咿呀的唱腔成了李牟雅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6岁那年,祖父带他去观看一场昆曲专场演出,当柳梦梅在台上吟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时,他竟看得痴了,演出结束后追着演员问“柳梦梅是怎么做到眼睛里会说话的”,这次 encounter 成为他与昆曲的“命中注定”,此后他缠着祖父学唱念做打,把家里的院子当舞台,用床单当水袖,模仿着戏中人的身段,一招一式竟有模有样。
12岁那年,李牟雅被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偶然发现,当时汪世瑜到当地选苗子,看到他在社区活动中心的表演,惊讶于这个孩子对人物情感的精准把握——他演《烂柯山》里的朱买臣,虽未经历世事,却把“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愤演绎得入木三分,汪世瑜当场决定收他为徒,李牟雅由此离开家乡,进入戏校系统学习,戏校的日子是艰苦的,每天清晨五点就要吊嗓子,练功房的地砖被他磨得发亮,膝盖上的淤青从未消退,但他从未抱怨过,反而常常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研究传统剧本,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柳梦梅的‘痴’是深情,唐明皇的‘痴’是悔恨,同一个‘痴’字,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分量”,这种超越同龄人的思考力,让老师既欣慰又惊叹:这孩子不是在“学戏”,而是在“悟戏”。
以“情”为魂:舞台上的“千面角色”
李牟雅的表演,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技巧的炫技,而是“情”的注入,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从剧本中走出,带着呼吸与温度,在《牡丹亭·惊梦》中,他饰演的柳梦梅初遇杜丽娘,眼神从惊艳到痴迷,手指轻抚花枝的动作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水袖翻飞间是藏不住的爱慕,连台下的老戏迷都忍不住感叹:“这柳梦梅不是演出来的,是‘活’的!”有评论家评价:“李牟雅的表演,让观众相信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不是杜撰的浪漫,而是真实可感的人生。”
为了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他甚至“跨界”学习其他艺术形式,演《长生殿》中的唐明皇,他去研究唐代历史,观摩故宫里的古画,揣摩帝王的爱与痛;演《桃花扇》里的侯方域,他苦读明史,甚至去商丘侯氏故里寻访,感受“复社文人”的家国情怀,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他的表演突破了行当的局限——他本是“巾生”应工,却能把“官生”的沉稳、“雉尾生”的英武演绎得恰到好处,下表是他近年来塑造的代表性角色及其艺术特色:

| 代表剧目 | 角色 | 行当 | 艺术特色 | 观众评价 |
|---|---|---|---|---|
| 《牡丹亭》 | 柳梦梅 | 巾生 | 唱腔婉转,眼神戏极具感染力,将“痴情”演绎得既热烈又克制 | “柳梦梅的‘情’直抵人心,让人相信世间真有‘为情而死’的执着” |
| 《长生殿》 | 唐明皇 | 官生 | 台风沉稳,水袖功出神入化,从“爱江山更爱美人”到“悔不当初”的情感转变层次分明 | “把帝王的无奈与深情演到了骨子里,看完让人心疼” |
| 《桃花扇》 | 侯方域 | 雉尾生 | 念白铿锵有力,身段兼具文人的儒雅与书生的风骨 | “不是刻板的‘才子’,而是有血有肉、有家国情怀的复社文人” |
| 《玉簪记》 | 潘必正 | 巾生 | 唱腔融入“水磨腔”的细腻,与小道姑陈妙常的对手戏既含蓄又热烈 | “把古代男女的‘情愫’演得像江南的春雨,润物无声却深入人心” |
传承与创新:让昆曲“活”在当代
李牟雅深知,昆曲的传承不能只靠“老戏老演”,更需要与时代对话,2018年,他发起“昆曲进校园”计划,带着年轻团队走进中小学,用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讲故事——他们把《牡丹亭》改编成校园剧,让柳梦梅和杜丽娘成为“同窗”;用流行音乐元素重新编曲传统唱段,惊梦》的唱段加入轻快的吉他伴奏,竟让00后学生跟着哼唱,他还开设短视频账号,用vlog记录排练日常,甚至挑战用“戏腔”唱流行歌曲,粉丝量迅速突破百万,不少网友留言:“原来昆曲这么好听,以前是我‘不懂欣赏’!”
在舞台创新上,他大胆尝试“跨界融合”,2021年,他与现代舞合作推出《寻梦·牡丹亭》,将昆曲的身段与现代舞的自由流动结合,舞台背景用全息投影呈现“游园惊梦”的梦境场景,演出一票难求,有年轻人看完后激动地说:“这不是‘老古董’,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国潮’!”但他始终坚持“创新不离根”,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昆曲的“水磨腔”“口法”“眼神”等核心技艺从未改变,反而因为形式的多元,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戏曲长河中的“追光者”
从江南小镇的懵懂少年,到昆曲舞台的“定场诗”担当,李牟雅用短短十余年时间,完成了从“热爱”到“使命”的蜕变,他说:“昆曲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是流动的活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流向更远的未来。”他不仅活跃在舞台上,还收了十几个徒弟,常对他们说:“学戏先学做人,只有心里有‘情’,眼里才有‘戏’。”这个被称作“戏曲天才”的年轻人,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昆曲这颗古老的明珠,在新时代的光芒下,愈发璀璨。
FAQs
Q1:李牟雅为何能被称为“戏曲天才”?他的天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A:李牟雅的天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悟性超群”,他学戏不靠死记硬背,而是能快速抓住角色的情感内核,12岁演《烂柯山》就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共情力;二是“可塑性强”,他虽以巾生为主,却能驾驭官生、雉尾生等多个行当,唱腔、身段、念白均有极高完成度;三是“创新意识”,他能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元素结合,让昆曲吸引年轻观众,这种“守正创新”的能力在年轻演员中极为罕见。

Q2:李牟雅在传承昆曲艺术时,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是否担心过度创新会失去昆曲的本真?
A:李牟雅认为,“传统”是根,“创新”是叶,他坚持“内核不变,形式多元”:核心唱腔、口法、程式等传统技艺严格遵循师承,绝不随意改动;但在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比如用现代技术增强视觉效果、用短视频拓宽传播渠道,他常说:“创新不是为了‘改’,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走进来’,只有先让观众爱上昆曲,才能谈传承,就像一道老菜,我们可以换个漂亮的盘子,甚至调整摆盘,但味道不能变,否则就不是那道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