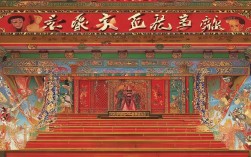豫剧《红果红了》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戏创作的经典之作,其音乐以浓郁的地方特色、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人物塑造,成为该剧艺术成就的重要支撑,而这部作品的作曲,正是河南省豫剧三团著名作曲家卢桂芬先生,他以对豫剧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合,为《红果红了》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使这部反映农村改革变迁的剧目在舞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卢桂芬先生从事豫剧音乐创作数十载,尤其擅长现代戏音乐创作,他始终秉持“戏曲音乐姓戏,更要与时俱进”的理念,在坚守豫剧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创新。《红果红了》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河南农村,讲述了主人公红果从保守固执到接受新思想、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转变历程,作曲家紧扣“变革”与“成长”的主题,将豫剧传统声腔与农村生活气息、时代精神紧密结合,构建了一个既“豫味”十足又充满现代感的音乐体系。
在传统板式的运用与创新上,卢桂芬展现了深厚的功力,豫剧以板式变化体为核心,二八板、慢板、流水板、飞板等板式是塑造人物、抒发情感的基础。《红果红了》中,作曲家并未简单套用传统板式,而是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情感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红果初登场时,面对村里发展苹果产业的提议,她内心充满犹豫与抵触,此时的唱段以【慢二八板】为基础,旋律低回婉转,节奏平稳舒缓,通过“顿音”和“滑音”的运用,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纠结与保守;而当红果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思想发生转变时,唱段则转为【流水板】与【垛板】的结合,旋律明快跳跃,节奏铿锵有力,特别是“红果儿红满山,日子比那蜜还甜”等核心唱句,通过高亢激越的【豫东调】旋律,将人物内心的喜悦与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下表为剧中主要板式及其艺术表现功能的对应关系:
| 板式类型 | 传统特点 | 剧中创新运用 | 代表唱段情感指向 |
|---|---|---|---|
| 慢二八板 | 速度舒缓,旋律抒情 | 加入装饰音,增强内心刻画层次 | 红果初期犹豫、保守 |
| 流水板 | 节奏明快,叙事性强 | 融入豫西调拖腔,增强地域特色 | 红果思想转变后的坚定 |
| 垛板 | 字多腔少,节奏紧凑 | 结合现代打击乐,突出戏剧冲突 | 村民争论改革方案时的激烈 |
| 【豫东调】快二八 | 高亢激越,情绪饱满 | 旋律线条简化,贴近口语化表达 | 红果成功后的喜悦与展望 |
唱腔设计是卢桂芬音乐创作的核心,他注重“以腔塑人”,通过不同声腔流派的融合与人物性格的结合,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剧中红果这一角色,作曲家大胆融合了常派(常香玉)的刚健有力与陈派(陈素真)的细腻委婉,既有“大腔大口”的豪迈,又有“小腔小口”的婉转,红果与父亲争论改革的一场戏,唱段以【豫东调】为主,旋律高亢但不失柔美,通过“腔随字走,字正腔圆”的处理,既展现了河南农村女性的泼辣坚韧,又流露出对父亲的孝敬与理解,而剧中其他角色,如思想开明的村支书、保守的老农等,也通过不同的声腔设计加以区分:支书的唱段融入【豫西调】的醇厚,体现基层干部的稳重;老农的唱则以【祥符调】的质朴为主,突出传统农民的固执与淳朴。
配器方面,卢桂芬在保留豫剧传统“三大件”(板胡、二胡、笙)的基础上,大胆引入西洋管弦乐和民族打击乐,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传统乐器中,板胡作为主奏乐器,其高亢明亮的音色贯穿全剧,既保持了豫剧的“根”;二胡与中阮的加入,则增强了旋律的层次感,特别是在抒情段落中,弦乐群的烘托使情感表达更为细腻,西洋乐器的运用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与民族乐器有机融合:如在小苹果丰收的场景中,圆号与竹笛的对话,营造出田园般的诗意;在矛盾冲突激烈的场面,定音鼓与板鼓的配合,则增强了戏剧的张力,这种“中西合璧”的配器方式,既满足了现代观众对音乐听觉的需求,又未偏离豫剧艺术的本质,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

主题音乐的创作是《红果红了》音乐的点睛之笔,卢桂芬以河南民间歌曲《编花篮》的旋律为素材,进行提炼与升华,创作出既熟悉又新颖的主题音乐,主题旋律简洁明快,以五声音阶为基础,节奏轻快活泼,象征着农村改革的活力与希望,这一主题在全剧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根据剧情变化进行变奏:在开场时,以明朗的弦乐齐奏呈现,预示着新事物的萌芽;在红果遭遇挫折时,主题旋律转为低沉的木管独奏,暗示困境;而在最终丰收的场景中,主题则与欢快的打击乐、人声合唱相结合,形成高潮,象征着改革成功的喜悦,主题音乐的贯穿与变奏,不仅统一了全剧的音乐风格,更深化了“变革带来新生”的主题思想。
卢桂芬的音乐创作还注重与舞台表演的深度融合,他根据演员的嗓音条件和表演特点,为“红果”的扮演者虎美玲量身定制唱腔,使其既有豫剧的“范儿”,又符合人物性格和演员的表演风格,在唱与念的衔接上,他强调“韵白与唱腔的统一”,使台词与音乐自然过渡;在舞蹈与音乐的配合上,则吸收了民间舞蹈的元素,如“摘苹果”“庆丰收”等场景,音乐节奏与舞蹈动作高度契合,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舞台效果,增强了剧场的观赏性。
《红果红了》自1994年首演以来,历经近三十年的舞台考验,其音乐艺术已成为豫剧现代戏创作的典范,卢桂芬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豫剧音乐的时代魅力,更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证明了:传统戏曲的现代化,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精神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唯有根植于传统、面向时代,戏曲艺术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生命力。
相关问答FAQs
Q1:《红果红了》的作曲为何能体现豫剧的现代转型?
A1:《红果红了》的作曲卢桂芬在坚守豫剧传统板式、声腔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一是配器上结合西洋管弦乐与传统民族乐器,丰富音乐层次;二是唱腔设计上融合不同流派特色,贴近现代人物情感表达;三是主题音乐以民间素材创新变奏,强化时代感,这些创新既保留了豫剧的“豫味”基因,又满足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了豫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Q2:卢桂芬在创作《红果红了》音乐时,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A2:卢桂芬的平衡体现在“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守正”即以豫剧传统板式(如二八板、流水板)为基础,遵循“腔随字走、字正腔圆”的戏曲规律,保留“三大件”乐器的核心地位;“创新”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板式节奏进行现代化处理(如加快垛板节奏增强冲突感)、引入西洋乐器丰富和声、将民间旋律提炼为主题音乐,他强调“创新不离其宗”,所有改动都服务于人物塑造和剧情表达,确保音乐既新颖又不失豫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