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讽刺科举制度的经典篇章,自清代吴敬梓笔下诞生以来,便以其鲜活的人物形象与深刻的社会批判,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共鸣,当这部文学经典被搬上京剧舞台,便在唱念做打的程式化表达中,赋予了范进这一角色更为立体的生命张力,而京剧艺术家顾谦以其对人物内心的精准把握与独具匠心的舞台呈现,让范进的“疯癫”背后,折射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剧,也为京剧《范进中举》的艺术高度奠定了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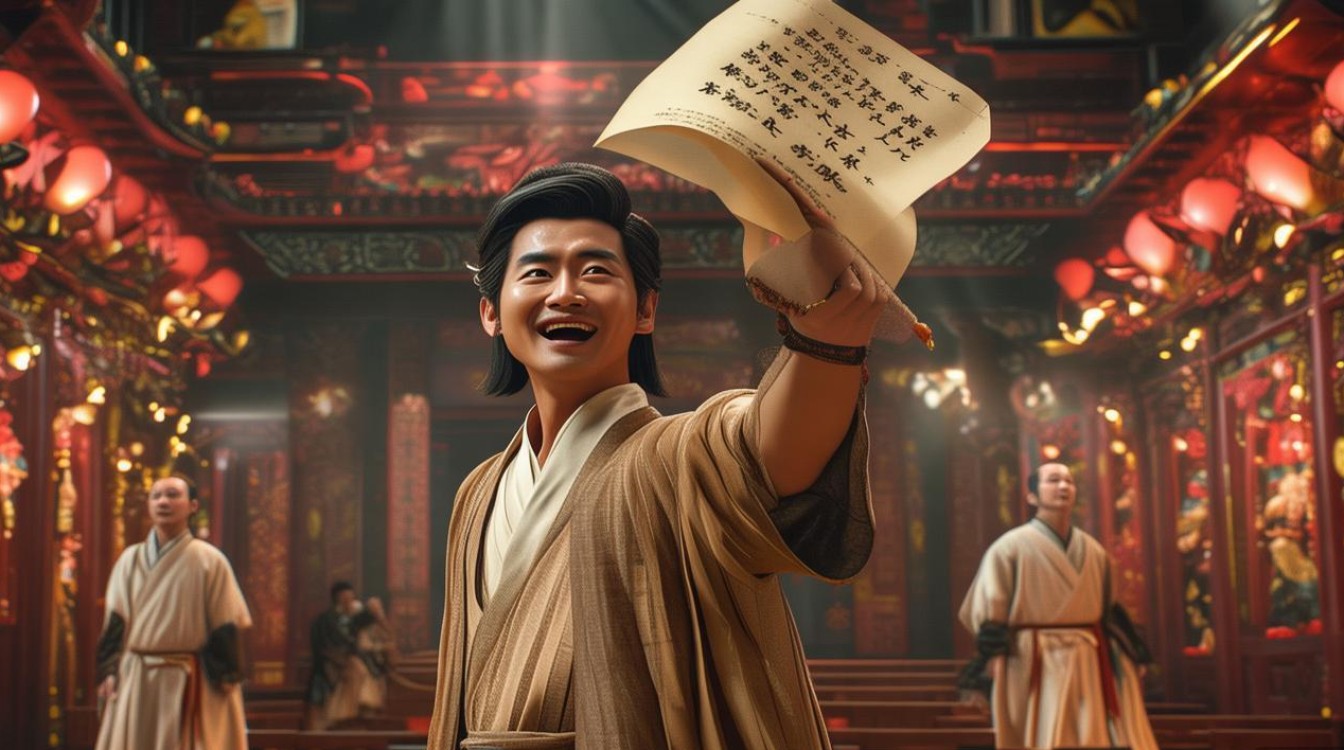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遭遇——五十四岁不第的潦倒,中举后喜极而疯,胡屠户从鄙薄到谄媚的转变,乡邻从漠然到趋炎附势的嘴脸——不仅讽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更揭示了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背后的世态炎凉,原著中范进的疯癫是“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文字简洁却张力十足,为舞台改编留下了广阔空间,京剧作为以“歌舞演故事”为特征的剧种,需将文学叙事转化为可视可听的表演艺术,其改编既要保留原著内核,又要符合京剧“唱念做打”的程式规范。
京剧《范进中举》的剧本改编,在情节上忠实于原著主线,但强化了戏剧冲突的层次感,开篇即展现范进家徒四壁的窘境:身穿破旧襕衫,鬓发斑白,面对妻子的埋怨与丈人胡屠户的当街辱骂,唯唯诺诺,连声“岳父教训的是”,通过“躬身”“袖手抖动”等身段,将其懦弱、压抑的性格外化,中举情节的处理则极具舞台张力——报帖传来时,范进正在灶房烧火,听闻“高中”二字,先是一愣,手中火钳“当啷”落地,随即眼神骤亮,继而狂笑、疯癫,这一系列动作通过“甩袖”“蹉步”“甩发”等程式衔接,将“喜极而疯”的心理转折具象化,胡屠户的态度转变,则通过“提刀骂”到“搓手笑”的念白变化,配合“髯口功”(捋髯、抖髯)的运用,将市侩小人物的势利刻画得入木三分。
唱腔与念白是京剧塑造人物的核心手段,范进的形象在不同唱段中逐渐丰满,中举前,他多以“二黄原板”或“二黄慢板”抒发郁结之情:“寒窗十载空对月,青丝熬尽两鬓斑”,唱腔低沉婉转,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显其穷困潦倒,又藏不甘之志;中举后转为“西皮流水”与“西皮快板”,如“中了!中了!我中了啊!”,节奏由慢到快,音调层层拔高,至“金榜题名”处突然拔尖,仿佛精神弦线绷断,模拟出狂喜到失控的听觉冲击,疯癫场次则以“散板”为主,唱词破碎,音调忽高忽低,如“噫!好!我中了!”一句,重复时加入“炸音”(突然拔高的声音),配合眼神呆滞、四肢抽搐的身段,将精神崩溃的悲剧感推向高潮。

| 表现维度 | 文学原著(《儒林外史》) | 京剧改编 |
|---|---|---|
| 叙事方式 | 文字描写,以叙述者视角展开内心活动 | 舞台表演,通过唱、念、做、打直接呈现情节 |
| 人物塑造 | 细腻的心理刻画,如范进中举前的绝望、中举后的狂喜 | 程式化动作与唱腔结合,如“甩袖”“踉跄”表现疯癫,“髯口功”表现胡屠户的市侩 |
| 冲突表现 | 以对话和细节暗示社会关系,如胡屠户“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 通过群戏强化冲突,如报喜人敲锣打鼓、乡邻争相道贺与范进疯癫的对比 |
| 主题呈现 | 讽刺性语言直接揭露科举弊端,如“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沦为功名的奴隶” | 通过舞台调度与人物关系隐喻,如范进跪拜时众人后退,暗示世态炎凉 |
在京剧《范进中举》的舞台上,顾谦的表演堪称“范进”形象的典范,他并未将这一角色简单归为“疯子”或“书呆子”,而是深入挖掘其“被科举异化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顾谦的表演有三大特点:一是“以形传神”,通过眼神的细微变化展现心理轨迹——中举前眼神浑浊无光,低头时眼角微微抽动,压抑着三十年的不甘;中举瞬间眼神骤然放大,瞳孔收缩,随即转为呆滞,精准捕捉了“喜极而疯”的心理转折,二是“唱腔为心”,他创新性地将“老生唱腔”的苍劲与“丑角念白”的诙谐融合,范进疯癫时的唱段,既保留老生的醇厚,又加入沙哑的颤音,如“中了!中了!我中了啊!”一句,尾音拖长且突然拔高,仿佛精神弦线绷断的瞬间,让观众在听觉冲击中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崩溃,三是“细节致胜”,他在表演中加入了“颤抖的手”这一标志性动作——范进接过报帖时,手指先是不受控制地抖动,随后整个手臂剧烈摇晃,甚至握不住薄薄一张纸,这个细节将“长期压抑后突然释放”的生理反应具象化,成为舞台经典,顾谦的范进,不是简单的“疯”,而是“被功名压垮的清醒者”:他的狂笑中带着悲凉,疯癫中藏着对命运的无声质问,让这一角色超越了原著的讽刺意味,升华为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悯。
京剧《范进中举》通过文学经典的舞台转化,让范进的故事超越了文本,成为审视封建科举制度的文化符号;而顾谦以其对人物悲剧性的深刻理解与精湛的舞台技艺,为这一角色注入了灵魂,他的表演不仅是对京剧程式的运用,更是对人性悲剧的叩问,让今天的观众依然能在范进的“疯癫”中,看到被异化的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挣扎。
FAQs

问题1:京剧《范进中举》中,范进的疯癫是如何通过表演手法体现的?
解答:范进的疯癫在京剧表演中通过多重手法综合呈现,唱腔上,中举前用低沉压抑的二黄慢板,中举后转为高亢激越的西皮流水,疯癫时则以节奏散乱、音调嘶哑的散板和摇板,模拟精神失控的状态;身段上,演员通过“甩袖”“踉跄”“手舞足蹈”等夸张动作,配合眼神由呆滞到涣散的变化,强化“疯”的戏剧性;念白上,采用“炸音”(突然拔高的声音)和“颤音”(抖动的尾音),表现喜极而悲的情绪转折,群戏对比(如众人道贺与范进疯癫的并置)也进一步烘托了其疯癫的悲剧色彩。
问题2:顾谦塑造的范进形象与其他演员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解答:顾谦塑造的范进独特之处在于“悲剧内核的深度挖掘”,不同于部分演员侧重表现范进的滑稽或疯癫,他更强调人物被科举制度异化的悲剧性,表演中,他通过“颤抖的手”“细微的眼神变化”等细节,展现范进长期压抑后的心理崩溃;唱腔上创新融合老生与丑角特点,既保留知识分子的清高,又突出底层小人物的卑微;念白中注入苍凉感,让“我中了”的狂喜背后,透出“一生为功名所困”的无奈,这种“悲喜交织”的演绎,使范进形象更具人文深度,超越了单纯的讽刺,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