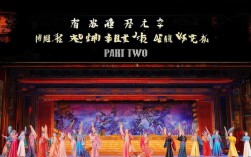“过昭关”是京剧传统剧目《伍子胥》中的核心片段,取材于《东周列国志》第五回“伍员跋涉过昭关”,讲述了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冤杀,历经千辛万苦逃亡至昭关,关口盘查严密,他一夜愁白头发,最终在隐士东皋公的帮助下设计过关的故事,这一片段以其跌宕起伏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塑造和精湛的表演艺术,成为京剧老生行当的“骨子老戏”,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彰显着传统戏曲的魅力。

剧情梗概:忠良之后的绝境突围
故事背景在春秋时期,楚平王听信谗言,冤杀伍子胥之父伍奢、兄伍尚,并下令画影图形捉拿伍子胥,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从楚国逃往吴国,途经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时,因地势险要、重兵把守,被拦截不得过,前有关隘,后有追兵,伍子胥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他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却在愁思中顿生转机——东皋公认出他是忠良之后,决定出手相助,东皋公门客皇甫讷与伍子胥相貌相似,便设计让皇甫讷假扮伍子胥过关故意被捕,真身则趁乱混出昭关,伍子胥成功逃脱,踏上复仇之路,奔向吴国。
这一片段的核心冲突是“绝境求生”,伍子胥的“忠”(对家族的忠诚)与“义”(对国家的愤懑)在昭关这一特殊空间中激烈碰撞,一夜白头的戏剧化处理,既是对人物心理的极致刻画,也为后续的过关突围埋下伏笔,让“忠义”主题在生死考验中愈发鲜明。
艺术特色:唱念做打的完美融合
“过昭关”的艺术魅力,集中体现在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运用上,尤其是老生行当的表演,将人物内心的焦虑、悲愤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
唱腔:以情带声,字正腔圆
伍子胥的核心唱段“一轮明月照窗前”(西皮慢板)是京剧经典唱腔之一,这段唱腔通过舒缓而深沉的节奏,表现伍子胥被困昭关时的辗转反侧:开篇“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以景起兴,用明月的清冷反衬内心的煎熬;随后“实可恨,平王无道,听信了,无义谗言”,旋律渐强,字字含恨,将他对楚平王的愤懑倾泻而出;而“恨平王,无道,斩我满门,冤仇大,似海深”一句,通过拖腔和颤音,将悲愤情绪推向高潮,唱腔中“慢板”的沉稳与“流水板”的急促交替,既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一夜未眠),也暗示了人物情绪的起伏——从绝望到顿悟,最终坚定过关决心。
念白:抑扬顿挫,传情达意
念白是京剧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伍子胥的念白以韵白为主,兼具京白的口语化特点,面对东皋公的试探,他念出“俺伍员,乃楚国逃犯,关津盘查甚严,如何能过?”时,语气中带着警惕与急切;而谈及家仇时,则咬牙切齿“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字字铿锵,凸显其刚烈性格,东皋公的念白则更显从容,通过“先生不必忧虑,某自有良策”等语句,塑造出仗义疏财、智勇双全的隐士形象。

做打:身段传神,化用程式
“一夜白头”是片段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做功,演员通过甩发、揉脸、眼神等技巧,表现伍子胥从黑发到白发的变化:先以双手抓揉头发,再猛地甩开发辫,配合眼神从迷茫到震惊的转变,将“愁白头”的戏剧夸张转化为舞台真实,过关时的“抢背”“吊毛”等跌扑技巧,则展现了他为逃亡不惜性命的决绝——当皇甫讷被捕、追兵逼近时,伍子胥一个“抢背”翻滚在地,随即起身疾奔,身手敏捷而充满张力,让观众直观感受到“过关如过鬼门关”的惊险。
人物塑造:忠义精神的立体呈现
伍子胥是“过昭关”的核心人物,他的形象并非单一的“复仇者”,而是集忠、孝、义、勇于一体的复杂个体,他对楚平王的暴政充满愤恨,誓言“灭楚兴吴”;他对家族的忠诚贯穿始终,逃亡途中不忘“父兄之仇”,甚至在过关后仍对东皋公叩拜“大恩来世再报”,这种“忠”与“义”的统一,让人物摆脱了脸谱化的刻板,展现出人性的深度。
东皋公作为关键配角,同样是“义”的化身,他虽为隐士,却深明大义,认出伍子胥后不计个人安危,设计助其过关,他的形象与伍子胥的“悲愤”形成对比,代表了民间对“仗义相助”的推崇,也让“忠义”主题从个人悲剧升华为民间道义的共鸣。
流派演绎:各具特色的艺术传承
京剧流派纷呈,“过昭关”在不同流派名家的演绎下呈现出多样风格,以下是几位代表性老生流派的表演特点对比:
| 流派代表 | 唱腔特点 | 表演侧重点 | 经典处理方式 |
|---|---|---|---|
| 余叔岩(余派) | 苍劲挺拔,刚柔并济,讲究“脑后音” | 注重人物内心刻画,身段沉稳 | “一轮明月”唱腔中融入“擞音”,表现愁绪的深沉 |
| 马连良(马派) | 潇洒流畅,俏皮生动,善用“巧腔” | 身段灵活,表情丰富 | 一夜白头时通过眼神与水袖的配合,展现从绝望到希望的情绪转折 |
| 谭富英(谭派) | 清亮醇厚,吐字清晰,节奏明快 | 台词干净利落,武功扎实 | 过关时的“吊毛”动作轻盈利落,突出逃亡的紧迫感 |
这些流派的演绎,既保留了“过昭关”的核心情节与精神内核,又融入了艺术家的个人理解,形成了“一戏多演、各具千秋”的传承局面,也让经典剧目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生。

文化内涵:忠义精神的现代回响
“过昭关”之所以历经百年仍被观众喜爱,不仅因其艺术精湛,更因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忠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伍子胥“为父报仇”的行为,在封建伦理中被视为“孝”的极致,而对国家昏聩的反抗则暗含“忠”的担当,这种精神在当代仍有启示意义——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不拔,面对不公时的挺身而出,始终是中华民族推崇的品格。
“过昭关”的戏剧化处理(如一夜白头)体现了京剧“虚实结合”的美学追求:既不拘泥于历史细节的真实,又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真实,这种“以形写神”的创作理念,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所在。
相关问答FAQs
Q1:“过昭关”中“一夜白头”的情节是否真实历史?
A1:“一夜白头”是民间传说与艺术加工的结果,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确有逃亡昭关的经历,但“一夜白头”并无史料明确记载,这一情节是京剧为强化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而进行的艺术创造,通过夸张手法展现伍子胥内心的极端焦虑,既符合人物情感逻辑,也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是京剧“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体现。
Q2:为什么“过昭关”被称为老生行当的“试金石”?
A2:“过昭关”对演员的唱、念、做、打要求极高:唱腔上需驾驭西皮慢板、流水板等多种板式,情感表达需从悲愤到坚定层次分明;念白需通过韵白与京白的结合展现人物性格;做功中“一夜白头”“跌扑抢背”等技巧考验演员的肢体控制与情绪传递;伍子胥这一角色年龄跨度大(从中年到老年感),心理复杂,需演员具备深厚的生活体验与艺术功底,能否演好“过昭关”,成为衡量老生演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故有“试金石”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