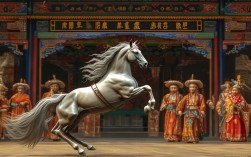《人欢马叫》作为豫剧现代戏的经典之作,自1963年首演以来,便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该剧以农村合作化时期为背景,通过饲养员一家人的故事,展现了集体经济的蓬勃活力与农民思想的深刻转变,而剧中的唱段作为戏曲艺术的灵魂,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更以生动的语言、巧妙的唱腔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连接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剧中的唱段紧扣人物性格与时代特征,各具特色,老饲养员常有富的唱段质朴深沉,充满对集体财产的热爱与责任感,例如在“马棚一夜”一场中,他抚摸着枣红马轻声吟唱:“枣红马,我的好伙伴,风里来雨里去你立下汗马功劳,草料要精,饮水要暖,我把你当作亲生的儿女一般。”唱词口语化却饱含深情,慢板的运用让旋律如溪水般缓缓流淌,配合唐喜成“唐派”唱法中真假声的转换,将老人对马的疼惜、对集体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儿子刘自鸣的唱段则充满青年人的朝气与转变的痕迹,起初他对集体劳动有抵触,唱词中带着几分抱怨:“早起贪黑图个啥?工分不够养活家。”而当他在父亲的感染下思想转变后,唱腔转为明快:“集体的道路宽又广,俺农民心里亮堂堂,汗水浇出幸福果,跟着党奔向前方!”二八板的节奏由缓到急,音调逐渐上扬,生动体现了他从迷茫到坚定的成长轨迹,儿媳小进的唱段则活泼灵动,充满劳动女性的热情,在“田间欢歌”中,她挥舞锄头唱道:“手拿锄头笑开颜,丰收的喜讯传得远,棉花白,粮食黄,集体生活比蜜甜!”豫东调的高亢嗓音配合快二板的节奏,如清泉般跳跃,将农村丰收的喜悦和妇女的乐观精神感染力十足。
从唱腔艺术来看,《人欢马叫》的唱段既保留了豫剧梆子腔的激越豪放,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细腻情感,板式运用上,慢板适合抒情,如老饲养员深夜照料马匹时的唱段,旋律舒缓,字字深情;快板则用于叙事,如小进描述田间劳作的情景,节奏明快,字句铿锵;而散板的穿插则增强了戏剧张力,如父子冲突时的对唱,旋律自由起伏,情绪跌宕起伏,唐喜成等艺术家在演唱中,将豫东调的“大滑音”“小跳音”技巧融入现代戏唱腔,既保持了戏曲的韵味,又让唱腔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唱段的语言特色同样值得称道,编剧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口语化表达,大量运用方言俗语,如“汗珠摔八瓣”“心里亮堂堂”等,既接地气又充满生活气息,唱词注重押韵与对仗,如“枣红马,千里志;草料足,精神爽”,短句工整,朗朗上口,便于传唱,修辞手法上,比喻、排比等手法的运用让唱词生动形象,如“集体是咱根和本,离开它就像树断根”,用“树根”比喻集体的重要性,通俗易懂又深入人心。

这些唱段在剧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们不仅串联起“马棚风波”“田间争辩”等关键情节,更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合作化时期农民思想的碰撞与升华,老饲养员的唱段强化了他“爱马如命、爱社如家”的典型形象;儿子的唱段则折射出一代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的成长;儿媳的唱段更是以女性的视角,为集体主义主题增添了温暖亮色,可以说,正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唱段,让《人欢马叫》超越了普通现代戏的范畴,成为一部既能体现戏曲美学,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
| 唱段段落 | 演唱人物 | 核心情感与唱腔特点 |
|---|---|---|
| “马棚一夜” | 常有富 | 情感:对枣红马的疼惜与对集体的责任感;唱腔:慢板,低回婉转,真假声结合,质朴深沉。 |
| “思想转变” | 刘自鸣 | 情感:从个人抱怨到集体认同的转变;唱腔:二八板转快二八,节奏渐强,明快坚定。 |
| “田间欢歌” | 小进 | 情感:劳动喜悦与集体自豪;唱腔:豫东调,高亢明快,甩腔活泼,充满感染力。 |
FAQs
-
问:《人欢马叫》的唱段为何能成为现代戏的经典?
答:其经典性源于三方面:一是题材贴近农村生活,唱段真实反映了农民的情感与时代变迁;二是唱腔创新,在保留豫剧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音乐元素,更具时代感;三是人物塑造鲜活,唱段与人物性格高度统一,如老饲养员的质朴、青年的朝气,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
问:老饲养员的唱段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什么特点?
答:老饲养员的唱段通过“以马喻人”“以情动人”的方式塑造形象,唱词中“枣红马是我的命根子”等表述,将爱马与爱集体巧妙结合;唱腔上采用慢板与低音区,突出其沉稳、忠厚的性格;细节描写如“半夜起来添草料”,更是通过具体行动展现了他“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使人物立体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