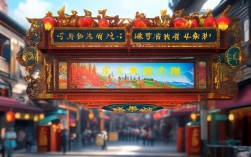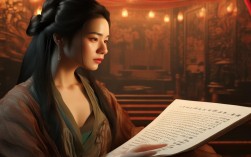晋剧《于成龙》的锣鼓声还在耳边回响,舞台上那位身着旧布袍、目光如炬的官员,用一生的清正廉洁刻下了“于青菜”的千古之名,两个多小时的戏曲演绎,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让我不仅看到了一个清官的群像,更触摸到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深刻内核,于成龙的故事之所以能跨越三百年仍打动人心,正在于戏曲用艺术化的手法,将“清廉”“爱民”“刚正”这些抽象品质,转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让观众在悲欢离合中读懂何为“父母官”的真谛。

戏曲中的于成龙,始终带着“泥土气”,他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舞台背景是瘴疠横行的荒蛮之地,演员用蹒跚的步伐和粗糙的布衣,勾勒出这位异乡官员的艰难处境,面对当地豪强的强征暴敛,他没有选择“和光同晦”,而是带着简陋的案卷深夜走访,用方言与百姓沟通——这些细节没有刻意拔高,却让“清廉”二字有了温度,当他在堂上拍案而起,将搜刮的粮食全部分给饥民时,高亢的唱腔与百姓的哭声交织,分明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生动注脚,这种“接地气”的塑造,打破了传统清官“高大全”的刻板印象,让于成龙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是在权力面前选择了“不普通”的坚守。
更动人的是戏曲对“爱民如子”的诠释,有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于成龙任两江总督时,微服私访发现富商勾结官府囤积居奇,导致米价飞涨,他没有直接抓人,而是脱下官袍,混入米市听百姓议论,当一位老妇捧着发霉的糠饼痛哭“活不下去”时,他背过身去,肩膀微微颤抖——这一刻,总督的威严与父亲的悲悯融为一体,后来他开仓放粮,与百姓同吃糙米粥的情节,舞台上没有宏大配乐,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和演员朴实的表演,却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戏曲没有回避现实的残酷,反而用“共情”让观众明白:真正的清廉,从不是冷冰冰的纪律约束,而是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的自觉。
刚正不阿的风骨,则是于成龙形象的“脊梁”,剧中有一处冲突高潮:他的上司——朝廷权臣索额图,以“办事不力”为由命他罢赈灾粮,并暗示“朝廷自有考量”,面对权压,于成龙没有卑躬屈膝,而是捧起赈灾账本一字一句道:“大人,这账本上写的是人命,不是朝廷的脸面!”演员的眼神从隐忍到坚定,唱腔从低沉到激昂,将“士大夫”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简单的“好人战胜坏人”,而是展现了在体制困境中,一个官员如何用良知对抗权力、用原则守护道义,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让“刚正”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为了让感受更直观,不妨将戏曲中的经典情节与精神内核对应如下:
| 戏曲情节 | 精神内核 | 艺术手法 |
|---|---|---|
| 赴任罗城时轻装简行,拒收下属“仪程” | 清廉自守 | 对比(当地官员的奢华与于成龙的简朴) |
| 微服私访,与百姓同吃糙米粥 | 爱民如子 | 细节(演员的肢体语言与表情) |
| 顶住压力开仓放粮,怒斥权臣囤积居奇 | 刚正不阿 | 冲突(个人良知与权力压迫的对抗) |
走出剧场,暮色中的城市霓虹闪烁,与舞台上的油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于成龙的故事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下的意义,当我们在新闻中看到“打虎拍蝇”的成果,读到“时代楷模”的事迹时,何尝不是在见证新的“于成龙”?戏曲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它将历史人物的精神密码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审美体验,让“清廉”“为民”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而是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
这场戏让我明白,真正的“清官”从不是神话,而是在权力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正如戏中于成龙那句反复吟唱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不仅是他的人生写照,更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把人民放在心上,永远是一个官员最珍贵的“官德”。

FAQs
Q1:戏曲中的于成龙与历史上的于成龙有哪些异同?
A1:戏曲中的于成龙以历史原型为基础,进行了艺术化加工,相同点在于核心精神一致,如历史上的于成龙确实以清廉、爱民著称,有“于青菜”的绰号,任期内多次为民请命;不同点在于戏曲通过集中矛盾、强化冲突(如与权臣的直接对抗)来增强戏剧性,而历史中的于成龙更多是在日常行政中体现清廉,如拒绝馈赠、简朴生活等,戏曲的“典型化”处理让人物形象更鲜明,但本质精神未变。
Q2:观《于成龙》这类清官戏,对当代青年有哪些启示?
A2:启示青年“初心”的可贵,于成龙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原则,提醒青年在成长中要保持理想与良知,不为名利所惑,传递“担当”的力量,戏曲中他主动深入民间解决问题,而非“躺平”,激励青年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作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理解“清廉”的现代意义——不仅是官员的操守,更是每个人面对诱惑时的底线意识,对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