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经千年发展,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历代文人墨客、艺术家、学者乃至外国友人对戏曲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深刻评价,这些评价不仅勾勒出戏曲的艺术特质,更折射出不同时代对美的认知与文化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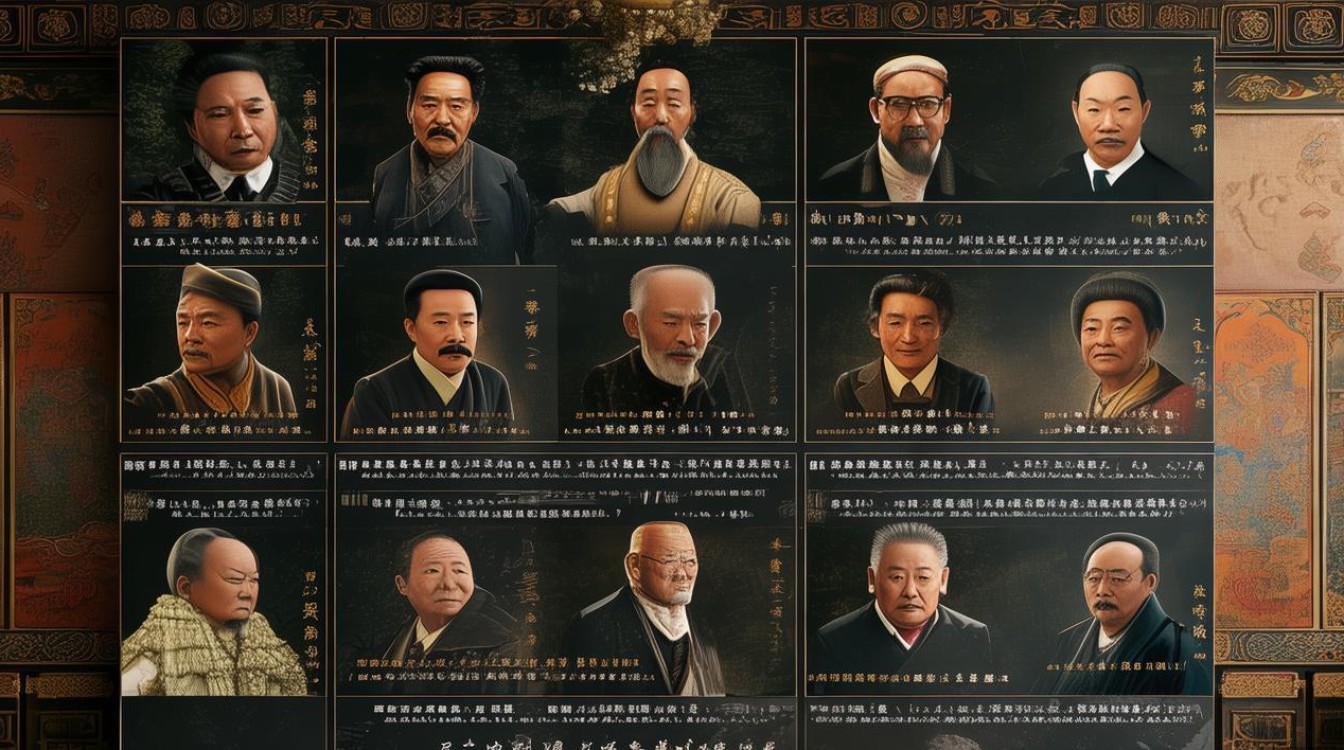
古代文人的审美观照:以情动人,以文化人
古代文人多将戏曲视为“小道”中的“大道”,在品评中既重其文学性,亦赞其舞台感染力,明代汤显祖以“至情”论曲,提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牡丹亭》题词,认为戏曲是传递人类情感极致的媒介,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之恋,将“情”置于“理”之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成为明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清代李渔则在《闲情偶寄》中系统归纳戏曲创作规律,强调“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主张戏曲应“贵浅显”“重机趣”,认为好的戏曲既要“雅俗共赏”,又要“能于浅处见才”,这对后世戏曲创作影响深远,元代关汉卿则以“本色当行”著称,其杂剧《窦娥冤》《救风尘》等直面社会现实,将市井人物的悲欢离合融入曲词,如“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珌一粒铜豌豆”的自白,既展现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也凸显了戏曲“针砭时弊、补益社会”的功能,元好问曾以“总观优孟衣冠处,最动人眼是铜琶”评价关汉卿的杂剧,道出了其作品中刚健质朴的艺术力量。
以下是部分古代文人戏曲评价的概览:
| 人物 | 时代 | 身份 | 核心评价观点 | 相关作品/事件 |
|---|---|---|---|---|
| 汤显祖 | 明代 | 文学家、剧作家 | “至情说”,戏曲是情感极致的表达 | 《牡丹亭》《临川四梦》 |
| 李渔 | 清代 | 戏曲理论家 | “结构第一”“贵浅显”,重舞台性与通俗性 | 《闲情偶寄》《风筝误》 |
| 关汉卿 | 元代 | 杂剧家 | “本色当行”,直面现实,展现市井精神 | 《窦娥冤》《救风尘》 |
| 王骥德 | 明代 | 戏曲理论家 | “本色”与“文采”平衡,论“曲之难” | 《曲律》《题红记》 |
近现代学者的学术建构:正名传统,厘清源流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戏曲研究逐渐从“品评”走向“学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首次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者也”,明确了戏曲“歌舞”与“故事”融合的本质特征,打破了“戏曲小道”的传统偏见,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他认为元杂剧“关、马、郑、白”之作“遂为千古之绝作”,肯定了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胡适则从“白话文学”视角出发,称关汉卿的杂剧“用的是当日的活的语言,说的是当日的活的人情”,强调戏曲是白话文学的重要源头,田汉作为现代戏剧奠基人,既继承传统戏曲的“写意精神”,又融入现代意识,提出“旧剧改革”应“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其《江汉渔歌》《白蛇传》等作品既保留了戏曲的程式美,又注入了时代精神,梅兰芳则以表演实践回应评价,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出“移步不换形”的传承原则,认为戏曲改革需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逐步创新,其“梅派”艺术将唱、念、做、打融为一体,成为京剧旦行表演的典范,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称赞他的表演“有超乎寻常的控制力,每个动作都是精确计算的完美”。

艺术家的实践体悟:程式与真情,技进乎道
戏曲艺术家在长期实践中,对“程式”与“真情”的关系有深刻体悟,程砚秋提出“声、情、美、永”的表演理念,认为“声是基础,情是灵魂,美是目标,永是追求”,强调唱腔需为情感服务,如《锁麟囊》中“春秋亭外风雨暴”的唱段,通过婉转低回的腔调展现薛湘灵的悲悯之心,盖叫天则主张“武戏文唱”,认为武打动作需有“戏”有“情”,如《十字坡》中孙二娘的“打店”,既展现武功的利落,又凸显人物的性格,尚长荣在塑造曹操、田光等角色时,突破传统行当限制,提出“以形传神、神形兼备”,将花脸表演的“粗犷”与“细腻”结合,拓展了戏曲现代戏的表现力,这些艺术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戏曲的“程式”不是束缚,而是提炼生活美的符号,需与“真情”融合,方能“技进乎道”。
外国友人的跨文化对话:东方智慧,世界共鸣
戏曲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外国友人的目光,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观看梅兰芳表演后,提出“间离效果”理论,认为中国戏曲通过“程化表演”(如虚拟的划船动作)让观众保持理性思考,这与西方戏剧“共鸣式”表演形成鲜明对比,为世界戏剧提供了新思路,卓别林曾评价梅兰芳:“您的表演既有高度的形式美,又能让情感自然流露,这是真正的艺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在《残酷戏剧》中提及中国戏曲的“符号化”表演,认为其“摆脱了语言和现实的束缚,直达人类潜意识”,这些评价印证了戏曲作为“世界语言”的可能性——它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跨越文化边界,引发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从汤显祖的“至情”到王国维的“正名”,从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到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名人对戏曲的评价既是艺术观念的碰撞,也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这些评价共同构建了戏曲的价值谱系:它是情感的容器,是历史的镜子,是美学的载体,更是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当代,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仍需从这些评价中汲取智慧——既要坚守“以歌舞演故事”的本质,也要拥抱创新;既要扎根民族文化土壤,也要走向世界舞台。

FAQs
Q1:为什么说王国维的“以歌舞演故事”定义了戏曲的本质?
A1:王国维的“以歌舞演故事”首次明确了戏曲的核心要素——“歌舞”(艺术形式)与“故事”(内容载体)的融合,此前戏曲常被视为“曲”的附庸或“技艺”的呈现,而该定义将其提升为“综合艺术”,指出戏曲既非单纯的歌舞,亦非纯粹的故事,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这一界定为戏曲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至今仍被广泛认可。
Q2:梅兰芳的“移步不换形”对当代戏曲传承有何启示?
A2:“移步不换形”强调戏曲改革需在“移步”(创新)中守住“不换形”(传统精髓),当代戏曲传承常面临“守旧”与“失本”的两难,梅兰芳的理念提示我们:创新可以尝试新题材、新形式,但戏曲的“四功五法”“程写意”等核心特质不能丢;只有守住艺术的“根”,创新才有生命力,如现代京剧《红灯记》在保留京剧唱腔、身段的同时,融入革命叙事,便是“移步不换形”的典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