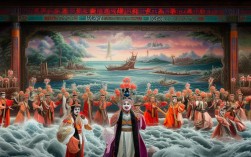京剧中骑驴的动作是传统表演艺术中极具特色的程式化技艺,它通过演员的身段、步法、眼神及道具的虚拟运用,将现实生活中的骑驴场景提炼为富有韵律美感的舞台表演,这一动作不仅考验演员的基本功,更需结合人物性格、剧情氛围进行艺术化处理,成为京剧“虚实相生”美学理念的生动体现。

骑驴动作的道具与虚拟化表现
京剧舞台上的骑驴表演从不使用真实毛驴,而是通过“无中生有”的虚拟手法让观众感知到驴的存在,传统道具中,曾有简易的布制驴形或竹编驴架,但更多时候演员仅凭肢体动作完成表演,最典型的辅助道具是“马鞭”——虽名为“马鞭”,但在骑驴场景中,演员会缩短鞭杆长度,或以手部虚拟动作替代执鞭,如拇指与食指捻动“缰绳”,手腕轻抖模仿“抖驴”,通过这些细节暗示骑驴状态,虚拟化的核心在于“以形写神”:演员需通过身体的晃动、步法的变换、眼神的专注,构建出“驴在身前,人在驴背”的空间感,让观众通过想象完成对“驴”的填补,这种处理既符合京剧“三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的写意传统,又为演员的表演留出了充分的艺术创作空间。
骑驴动作的细节分解与技巧
骑驴动作的表演可细化为“上驴—骑驴行进—下驴—驴的动态表现”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均有严格的程式要求,同时需结合人物情绪灵活调整。
上驴:演员侧身站立,目视“驴”的方向,双手先轻提衣襟(模拟整理鞍鞯),随后重心下沉,屈膝半蹲,同时做“蹬驴”状——右脚虚点地面,左脚向后微抬,仿佛踩上驴镫;接着身体向上轻轻一纵,顺势“坐”于虚拟驴背,整个过程需连贯轻盈,避免笨重,若表现女性角色(如花旦、青衣),上驴时可配合“掩面”“整鬓”等动作,增添娇俏或羞涩之态;男性角色(如老生、武生)则多挺胸抬头,动作沉稳有力,体现人物性格。
骑驴行进:这是骑驴表演的核心环节,步法的选择需根据“驴速”和场景变化,若表现慢行(如乡村小道),演员多采用“圆场步”的变体——步幅小、频率快,上身微微前倾,模仿驴背的颠簸感,双手或轻扶“鞍鞯”,或自然下垂,眼神平视前方,带出悠然自得之态;若表现急行(如赶路、逃难),则需加快步速,上身随步伐左右轻微晃动,同时配合“抖缰”“扬鞭”等动作,眼神专注警觉,营造出紧张氛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驴步”的细节:演员需以脚掌外侧先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形成轻微的“外八字”步态,这是模仿驴行走时特有的摇摆姿态,也是区分“骑驴”与“骑马”的关键——骑马步法多方正有力,而骑驴则更显轻巧灵活,带点“笨拙”的生活感。
下驴:动作与上驴相反,演员先“勒住缰绳”,身体后仰,做“停驴”状,随后左脚先落地,右脚顺势“离镫”,身体缓缓站直,最后转身回望“驴”,或轻拍驴背以示告别,细节中充满生活情趣。
驴的动态表现:除了骑者自身的动作,还需通过肢体语言表现驴的“情绪”,驴受惊时,演员会猛地向后一仰,双手张开作“失控”状,双脚快速踉跄步法,配合眼神的惊恐;驴打喷嚏,则可低头、甩头,同时发出“啊—嚏”的拟声词;驴慢行或歇息,则可让身体随节奏轻微上下起伏,双手轻拍“驴颈”,模仿抚摸牲口的动作,这些“拟驴”表演需自然融入人物动作,避免刻意夸张,达到“人驴合一”的境界。

不同行当的骑驴表演差异
京剧骑驴动作并非千篇一律,不同行当根据角色身份、性格特点,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表演风格。
花旦与闺门旦:此类角色多扮演年轻女性,如《红娘》中的红娘、《拾玉镯》中的孙玉姣,骑驴时步法轻快跳跃,上身挺直但略带娇憨,常配合“碎步”“小跳步”,双手多提着衣角或手帕,眼神灵动带笑,突出少女的活泼俏皮,红娘》中“拷红”后,红娘骑驴送信,步法急促却不凌乱,上身随步伐微微晃动,嘴角带笑,既表现了任务的紧迫,又透着对张生与崔莺莺的善意调侃。
青衣:多扮演端庄女性,如《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骑驴时步法沉稳缓慢,身板挺直,动作幅度小,双手或交叠于腹前,或轻扶鞍鞯,眼神低垂或远望,含蓄中透出悲凉,昭君骑驴出塞,步法如“行云流水”,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思乡的愁绪上,通过身体的轻微晃动模拟塞外风沙中的驴行,将“一去紫台连朔漠”的孤寂感融入动作之中。
老生与老旦:此类角色多为老年人,如《武家坡》中的王宝钏(老旦扮相)或《桑园会》中的秋胡(老生),骑驴时需弯腰驼背,步法拖沓,老生多拄拐杖,双手一执鞭一扶拐,眼神浑浊带疲惫;老旦则常一手“提襟”防止衣衫绊脚,一手“抖缰”,动作缓慢中带着倔强,武家坡》中王宝钏苦守寒窑后骑驴寻夫,步法踉跄,身体左右摇摆,模仿老驴的蹒跚,将岁月的沧桑与期盼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武生与武旦:此类角色需结合武功技巧,骑驴时更显英姿飒爽,如《扈家庄》中的扈三娘(武旦),骑驴时可融入“鹞子翻身”“侧身踢腿”等动作,步法刚劲有力,上身虽晃动但重心稳定,眼神凌厉,展现人物的武艺高强;武生则多在“趟马”基础上改良,骑驴时动作大开大合,如“挥鞭策驴”“马上劈叉”,将骑驴与武打结合,形成独特的“武戏文唱”风格。
音乐伴奏与骑驴动作的配合
骑驴动作的节奏感离不开音乐的烘托,京剧锣鼓经与唱腔的运用,能强化“驴”的动态和人物情绪,表现慢行时,多用“小锣抽头”或“南梆子”,节奏舒缓,配合演员的圆场步,营造出悠闲的氛围;表现急行或受惊时,则用“急急风”或“快长锤”,锣鼓密集急促,推动演员的步法和身段,形成紧张感;若表现驴打喷嚏或踢跳,可在锣鼓中加一声“钹”的脆响,或演员模仿驴叫的“咴儿”声,增强舞台的生动性,唱腔方面,若骑驴时有唱段,如《昭君出塞》中的“昭君马上思想想”,唱腔的婉转起伏需与骑驴的步法节奏同步,形成“载歌载舞”的艺术效果。

骑马与骑驴表演的对比
为更清晰体现骑驴动作的特色,可通过表格对比骑马与骑驴的表演差异:
| 表演要素 | 骑马动作 | 骑驴动作 |
|---|---|---|
| 道具 | 马鞭(长杆)、马头道具(部分剧目) | 短鞭或无鞭,以虚拟动作为主 |
| 步法 | 趟马步(大步、跨步,方正有力) | 驴步(小步、碎步,外八字,带颠簸感) |
| 身段 | 挺胸昂首,展臂扬鞭,姿态舒展 | 含胸收腹,身体微晃,动作生活化 |
| 节奏 | 多表现长途奔袭,节奏沉稳或激昂 | 多表现短途或生活场景,节奏轻快灵活 |
| 代表剧目 | 《长坂坡》《挑滑车》 | 《昭君出塞》《红娘》《武家坡》 |
相关问答FAQs
Q1:京剧中的骑驴动作为什么不用真驴,而要虚拟表演?
A:京剧艺术的核心美学是“虚实相生”,虚拟表演能突破舞台时空限制,让观众通过想象完成对“驴”的感知,更具艺术留白之美,真驴难以控制,可能影响演出节奏和演员安全,且京剧的程式化表演需要将生活动作提炼为规范化的“程式”,虚拟化更能突出人物情感和剧情氛围——例如昭君骑驴的悲凉、红娘骑驴的俏皮,均需通过演员的夸张与变形来强化,而非依赖真实牲口的自然状态。
Q2:不同流派的演员在表演骑驴动作时,会有哪些独特风格?
A:京剧流派的形成源于对程式的个性化诠释,骑驴动作亦如此,例如梅兰芳的梅派讲究“美”与“柔”,骑驴时身段圆润如“行云流水”,眼神含蓄,动作细腻,如《霸王别姬》中虞姬骑驴(虽非传统剧目,但可推演其风格),突出人物的端庄与哀婉;荀慧生的荀派则重“俏”与“活”,骑驴步法跳跃带“小颤”,表情丰富,如《红娘》中的表演,通过挤眉弄眼、甩手帕等动作,将少女的灵动与狡黠融入骑驴场景;周信芳的麒派(老生)则强调“刚”与“拙”,骑驴时弯腰驼背,步法顿挫有力,如《徐策跑城》中虽非骑驴,但其“跑城”的步法可类比骑驴的蹒跚,凸显老迈倔强的人物性格,这些流派风格的差异,正是京剧艺术“百花齐放”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