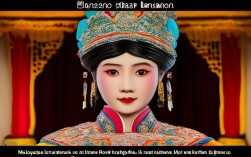道情戏曲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传统曲艺形式,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唐代道教道曲,后经民间艺人吸收地方民歌、说唱艺术演变而成,主要流行于山西、陕西、甘肃、河北等地,其表演形式以“渔鼓”“简板”为主要伴奏乐器,唱腔高亢苍凉、质朴豪放,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生活趣事,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是农耕文明背景下民众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当代道情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中,王晓玲的名字尤为突出,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其精湛的技艺、创新的精神和对艺术的坚守,为这一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王晓玲的艺术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自幼受家乡道情戏曲氛围熏陶,12岁考入甘肃环县道情剧团,师从著名道情艺人魏元成、敬登琨等,系统学习过程中,她不仅刻苦钻研传统唱腔的“平调”“十字调”“耍孩儿”等板式,更深入揣摩道情戏曲中“唱、念、做、舞”的融合技巧,尤其擅长通过眼神、身段展现人物内心,其早期代表剧目《梁祝》《劈山救母》中,她将道情唱腔的婉转与人物命运的悲苦结合,塑造的祝英台、三圣母等形象深入人心,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艺术领悟力,90年代,她突破传统局限,尝试将道情戏曲与现代审美结合,在《闹天宫》《清风亭》等剧目中融入舞蹈元素和舞台灯光技术,使古老的道情舞台更具视觉冲击力,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
王晓玲的艺术风格以“情”为核心,她认为“道情之魂在于情”,无论是慷慨激昂的历史叙事,还是细腻缠绵的儿女情长,她总能以声音为笔,勾勒出鲜明的人物画卷,她的唱腔兼具“老腔”的苍劲和“时调”的婉转,高音处如穿云裂石,低回时似溪水潺潺,尤其在运用“擞音”“颤音”等技巧时,既能精准传递人物情绪,又能保留道情戏曲特有的“土味”与“野趣”,表演上,她注重“以形传神”,如在《李逵探母》中,通过粗犷的台步、夸张的面部表情,将李逵的孝心与莽撞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花亭相会》中,则以水袖功和眼神的流转,演绎出才子佳人的含蓄深情,这种“千人千面”的塑造能力,使她成为道情戏曲界公认的“全能旦角”。
作为非遗传承人,王晓玲深知“守正创新”的重要性,她带领团队历时五年整理编撰《环县道情戏曲集成》,收录传统剧目68部、唱腔曲牌200余首,为道情戏曲的保存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她积极推动道情戏曲进校园、进社区,创办“道情小课堂”,培养青少年学员百余人,其中多人已在省级戏曲比赛中获奖,2018年,她发起“道情戏曲数字化保护工程”,利用现代技术录制经典剧目,建立线上数据库,让更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道情艺术,她还跨界尝试道情戏曲与现代音乐、话剧的融合,创作出《黄土谣》《丝路情韵》等新剧目,使道情戏曲从田间地头走向都市剧场,实现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

王晓玲对道情戏曲的贡献不仅在于技艺的传承,更在于她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她常说:“道情是黄土里长出来的艺术,离开了泥土,就没了魂。”数十年如一日,她拒绝商业演出的高价邀约,坚持深入基层为群众演出,年均下乡演出超百场,用最质朴的方式传递着传统文化的温度,她的努力不仅让道情戏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彰显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相关问答FAQs
Q1:道情戏曲与其他地方戏曲相比,有哪些独特的艺术特点?
A1:道情戏曲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伴奏乐器以“渔鼓”(竹制管身,蒙以鳄鱼皮或猪膀胱)和“简板”(两根竹板)为核心,音色古朴苍凉,形成“一鼓一板定节奏,渔鼓声中诉悲欢”的特色;二是唱腔结构自由灵活,不受固定宫调限制,常根据情感需要即兴发挥,具有浓郁的“山野之气”;三是表演形式兼具“曲艺”的叙事性和“戏曲”的综合性,既有“坐唱”的静态抒情,也有“走唱”的动态叙事,更贴近民间生活场景,这些特点使道情戏曲成为北方民间艺术中极具辨识度的“活化石”。

Q2:王晓玲在传承道情戏曲时,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A2:王晓玲的传承理念可概括为“守其根脉,融其新机”,在“守传统”方面,她严格遵循道情戏曲的“母调”体系,保留老艺人传下来的“起腔”“转腔”“落腔”等核心程式,确保艺术本真性;在“创新”方面,她从内容、形式、传播三方面突破:内容上,除传统剧目外,创作反映当代乡村生活的现代戏;形式上,融合现代舞台技术(如LED背景、立体声效)增强观赏性,同时创新舞蹈语汇丰富表演层次;传播上,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让年轻观众以更便捷的方式接触道情艺术,她强调“创新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让老艺术讲出新时代的故事”,这种平衡使道情戏曲既“守住了魂”,又“焕发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