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传统剧目中,并无名为《五家坡》的独立剧目,通常可能是对经典折子戏《武家坡》的笔误或误传。《武家坡》是京剧《红鬃烈马》中的核心折子戏,讲述了薛平贵与王宝钔历经十八年离散后,在武家坡重逢试探、夫妻相认的动人故事,是京剧老生、青衣行当的代表作之一,其“意思”不仅在于曲折的剧情,更在于对人物情感的深刻刻画、传统伦理观念的艺术呈现,以及京剧程式化表演的集中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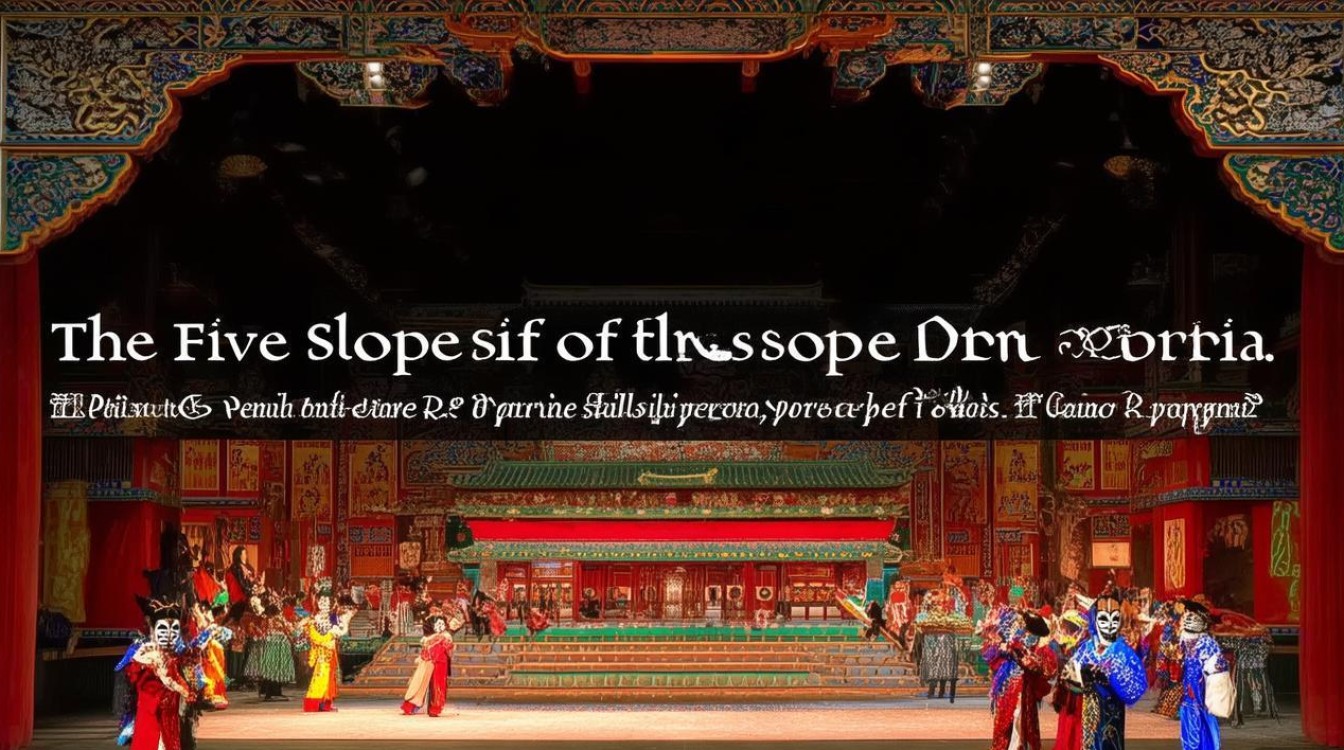
剧情梗概:十八年离散与试探重逢
《武家坡》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唐代,薛平贵因娶王允之女王宝钔被赶出家门,后从军征战,流落西凉,成为西凉王,而王宝钔苦守寒窑,独自抚养幼子,历经贫寒,十八年后,薛平贵逃离西凉,回到长安武家坡,恰遇王宝钔,此时王宝钔已形容憔悴,不识眼前落魄男子便是丈夫,薛平贵为试探妻子是否忠贞,谎称自己曾得宝钔赠银,助其从军,如今特来报恩,并编造自己已另娶妻室,王宝钔闻言悲愤交加,既痛恨丈夫“负心”,又念及旧日恩情,二人展开激烈对峙,薛平贵以当年信物为证,夫妻相认,共叙离情。
剧情的核心冲突集中在“试探”与“相认”两个环节:薛平贵以“陌生”身份试探,王宝钔以“坚贞”回应,这种身份错位下的情感张力,既是戏剧性的来源,也是人物性格的试金石,十八年的时空跨度,让重逢充满了沧桑感——薛平贵从贫寒公子到西凉王,身份逆转却不忘旧情;王宝钔从相府千金到寒窑苦守,命运跌宕仍守妇道,二人的情感在试探中历经波折,最终归于团圆,既满足了传统戏曲“善有善报”的叙事逻辑,也凸显了“忠贞不渝”的伦理主题。
人物形象:忠贞与试探的双重刻画
《武家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薛平贵与王宝钔两个人物的深度塑造,二者性格鲜明,情感复杂,构成了传统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夫妻关系”样本。
王宝钔:传统“贤妻”形象的极致演绎
王宝钔是京剧舞台上“青衣”行当的经典形象,其核心特质是“忠贞”,十八年寒窑苦守,她拒绝了无数富贵追求,靠挖野菜、缝补度日,这种坚守不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传统“妇德”的具象化,在《武家坡》中,她的情感变化层次分明:初见薛平贵时,因对方“陌生”且言语轻浮而警惕斥责;听闻其“另娶妻室”时,悲愤交加,既痛斥“负心汉”,又隐约存有旧情;最终通过信物确认身份后,瞬间转为委屈、激动与欣慰,从“怒”到“悲”再到“喜”,情感转折自然,展现了青衣行当“以情带声、以形传神”的表演精髓,她的唱段如“指着高声骂几声,无义的强盗骂几声”,通过高亢的“西皮导板”与悲愤的“西皮流水”,将满腔委屈倾泻而出,成为青衣唱腔的经典范例。
薛平贵:从“试探者”到“深情郎”的身份转变
薛平贵在剧中兼具“老生”的沉稳与“武生”的英气,其性格核心是“情义”,作为试探者,他明知妻子忠贞,却仍以“陌生”身份激化矛盾,这种“折磨”背后,是十八年分离的愧疚与对妻子坚守的敬畏,他的唱腔“一马离了西凉界”,通过明快的“西皮原板”与“西皮流水”,既展现了他西凉王的身份,又暗含对故土、对妻子的思念,面对王宝钔的斥责,他不辩解、不恼怒,而是逐步引导对方回忆往事,最终以“寒窑窑门你朝南开,不贞的妇人莫进来”的激将法,以及“罗裙当土盖,草绳系腰间”的信物,完成试探,这一过程中,他的情感从“试探”转向“心疼”,从“身份优越”回归“丈夫本分”,老生行当的“做派”(如捋髯、眼神变化)与唱腔的抑扬顿挫,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艺术表现:程式化表演与唱腔的融合
《武家坡》作为京剧折子戏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魅力,尤其以“唱”与“做”的融合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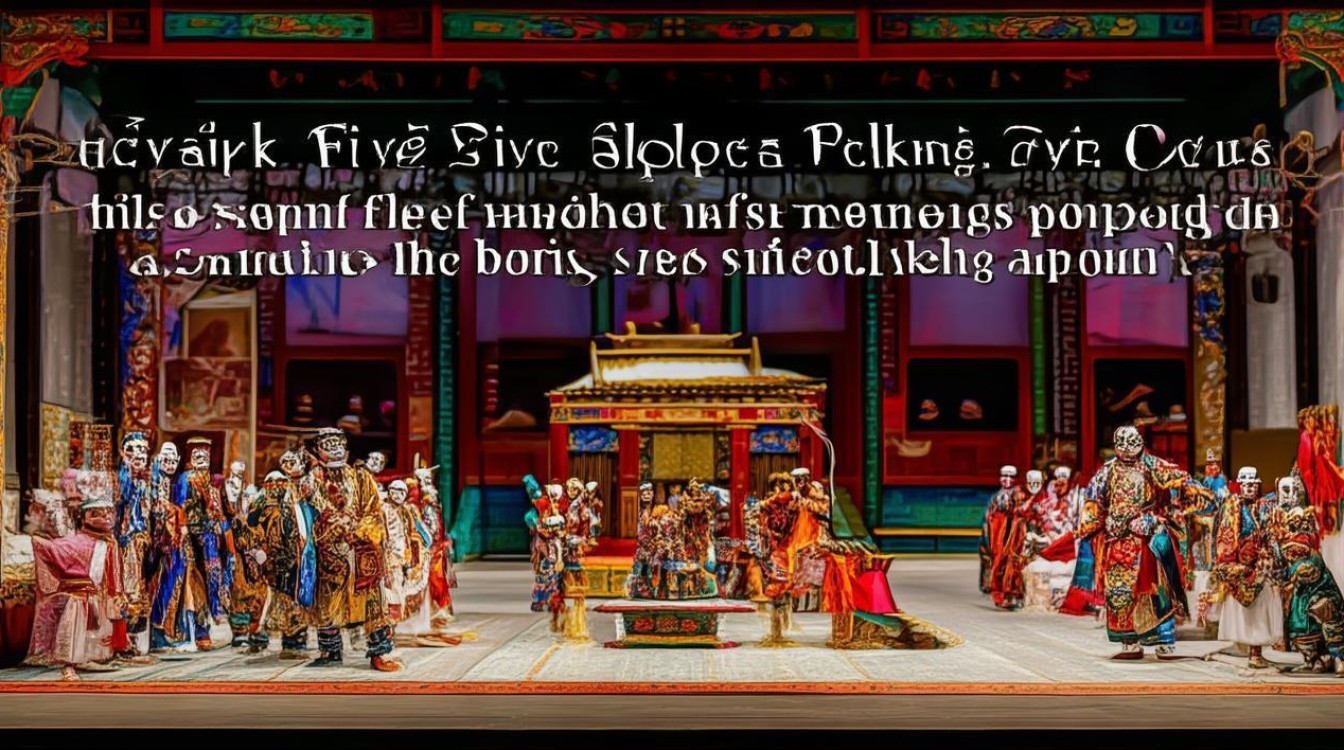
唱腔:板式变化与情感表达的统一
京剧唱腔讲究“因情设腔,以腔传情”,《武家坡》的唱段设计堪称典范,全剧以“西皮”声腔为主,通过不同板式的转换,配合人物情感起伏:
- 西皮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开篇散板,节奏自由,用于薛平贵初上场,展现其驰骋归来的豪迈与对故土的思念;
- 西皮原板:“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中速平稳,用于薛平贵回忆往事,情感内敛而深沉;
- 西皮流水:“你的父在朝中官居首相”——节奏明快,字字清晰,用于薛平贵试探时的“编故事”,语带调侃却暗藏机锋;
- 西皮散板:“夫妻们相会在寒窑内”——结尾散板,节奏舒缓,用于夫妻相认后的情感释放,既有喜悦,又有辛酸。
不同板式的衔接,如流水接散板、原板接导板,既符合京剧“声情并茂”的美学原则,也让人物情感的流动有了音乐的载体。
表演:程式动作与人物性格的契合
京剧的“做功”讲究“有程式、无定式”,即遵循固定的表演规范,又要根据人物性格灵活调整。《武家坡》中,两人的表演极具代表性:
- 王宝钔的“青衣做派”:持竹篮、挖野菜的动作(虚拟表演),眼神从警惕到悲愤再到惊喜的变化,以及听到“另娶妻室”时甩袖、顿足的身段,既符合青衣“端庄含蓄”的行当特点,又凸显了人物的刚烈与委屈;
- 薛平贵的“老生做派”:捋髯、背手、踱步的沉稳姿态,试探时眼神的闪烁与观察,以及相认后扶妻、拭泪的细腻动作,将“儒将”的风度与“丈夫”的柔情融为一体。
剧中的“对唱”是重要看点,两人通过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情感互动,如王宝钔斥责“强盗”,薛平贵回应“贤妹”,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暗藏情意,这种“对手戏”的张力,成为《武家坡》久演不衰的关键。
文化内涵:传统伦理的艺术折射
《武家坡》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艺术形式的完美,更在于它承载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与价值追求,通过戏曲的“美善统一”,让观众在审美中接受道德教化。
“忠贞”:传统妇德的极致推崇
王宝钔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妇德”的要求——从一而终、贫贱不移、坚贞不屈,十八年寒窑苦守,是对“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践行,她的“忠贞”不仅是个人选择,更被塑造为女性道德的楷模,这种塑造虽有时代局限性(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忽视),但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婚姻稳定的重视,以及对“患难与共”情感的肯定。

“情义”:男性责任与家庭观念的体现
薛平贵的“试探”,表面是对妻子的“考验”,实则是对自身“责任”的确认——他需要确认妻子的坚守,才能心安理得地履行丈夫的职责,而最终夫妻团圆,既是对王宝钔忠贞的回报,也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情义观,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虽然通过“试探”的曲折形式展现,但内核仍是传统家庭伦理中“相濡以沫”的理想。
“团圆”:传统戏曲的审美心理满足
《武家坡》的结局是“大团圆”,薛平贵与王宝钔历经磨难后终得团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剧中虽未直接写恶人,但王允的势利等作为隐性背景)的叙事,符合传统观众的审美心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圆满,通过戏曲舞台得以补偿,这种“情感宣泄”与“心理慰藉”,是传统戏曲重要的社会功能。
《武家坡》的艺术地位与传承
作为《红鬃烈马》中最具代表性的折子戏,《武家坡》自清代以来便是京剧舞台上的常演剧目,历经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张君秋等几代名家的打磨,形成了不同的表演流派,老生行当的“谭派”“余派”“马派”对薛平贵各有诠释,或重苍劲,或重儒雅,或重洒脱;青衣行当的“梅派”“张派”则赋予王宝钔不同的气质,或重温婉,或重刚烈,使得剧目在不同流派中焕发出多样的艺术魅力。《武家坡》仍是京剧演员的“开蒙戏”与“看家戏”,其唱腔、表演被纳入京剧教学的核心内容,成为传承京剧艺术的重要载体。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武家坡》和《算粮》《大登殿》是什么关系?
解答:《武家坡》是京剧《红鬃烈马》中的核心折子戏,与《彩楼配》《三击掌》《武家坡》《算粮》《大登殿》共同构成全剧,讲述薛平贵与王宝钔爱情故事的主线。《武家坡》侧重夫妻离散后的试探与相认,《算粮》写王宝钔代夫向丞相府讨要军粮,展现其智慧与勇气;《大登殿》则是薛平贵登基后封赏妻儿,故事圆满收场,三折戏环环相扣,《武家坡》是情感转折的关键,后两折则进一步深化了“忠贞得报”的主题,是传统京剧“骨子老戏”的代表组合。
问题2:为什么《武家坡》中薛平贵要试探王宝钔?
解答:薛平贵试探王宝钔主要有三重原因:一是身份悬殊带来的不安全感——他从军后成为西凉王,而王宝钔苦守寒窑,两人地位剧变,他需确认妻子是否因贫贱改嫁;二是十八年分离的疑虑——古代战乱频繁,信息闭塞,他需通过试探验证妻子的忠贞;三是戏剧冲突的需要——试探情节通过“夫妻不相认”的误会制造张力,既展现王宝钔的坚贞,也体现薛平贵从试探到相认的情感转变,推动剧情高潮,同时凸显传统戏曲“忠孝节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试探并非不信任,而是历经磨难后对情感的确认与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