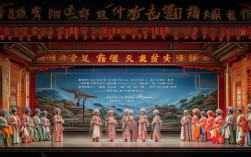京剧《审潘洪》是传统杨家将戏中的重要剧目,以北宋名将杨继业被奸臣潘洪陷害,其子杨延昭为父伸冤、最终潘洪被审问定罪为主线,展现了忠奸斗争的激烈冲突,剧中曲谱作为京剧音乐的核心载体,不仅承载着唱腔的旋律与节奏,更通过声腔的起伏变化、板式的转换搭配,精准传递人物情感与剧情张力,成为塑造角色、推动叙事的关键艺术手段。

京剧曲谱的记录方式以工尺谱为基础,结合板眼符号与唱词,形成一套完整的记谱体系。《审潘洪》的曲谱在传统“皮黄腔”框架下,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根据剧情需要灵活运用不同板式,杨延昭在公堂之上质问潘洪时,多采用【西皮导板】【西皮原板】【西皮快板】的组合:【导板】以散板形式开篇,音调高亢激昂,表现杨延昭悲愤交加的情绪;【原板】节奏平稳,叙述潘洪的罪状,逻辑清晰;【快板】则节奏加快,字字铿锵,体现杨延昭据理力争的坚定态度,而潘洪狡辩时,则多用【二黄慢板】【二黄原板】,旋律低回婉转,通过拖腔与装饰音的运用,刻画其色厉内荏、试图蒙混过关的心理状态。
在声腔设计上,《审潘洪》的曲谱注重“以声传情”,如杨延昭回忆父亲杨继业被围困两狼谷的唱段,【二黄导板】“忆昔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后接【回龙】“到如今子替父把冤伸”,旋律由高亢转入低沉,再通过【二黄原板】的铺陈,将杨家满门忠烈却遭奸佞陷害的悲愤与无奈层层递进地展现,潘洪在审讯中百般抵赖时,曲谱中频繁使用“擞音”“颤音”等装饰技巧,使唱腔显得刻意做作,与其虚伪人设形成互文,伴奏中的京胡、月琴、三弦等乐器与唱腔紧密配合,如【西皮流水板】中京胡的快弓拉奏,营造紧张氛围;【二黄慢板】中月琴的轮指伴奏,则增添唱腔的苍凉感。
板式的灵活转换是《审潘洪》曲谱的另一大特色,剧中“三堂会审”一场,通过【西皮导板】(潘洪初登场时的惊恐)→【西皮散板】(官员质问时的支吾)→【西皮快板】(杨延昭揭露罪证时的激愤)的板式递进,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下表为《审潘洪》主要声腔板式与情感表达的对应关系:

| 声腔 | 板式名称 | 节奏特点 | 情感功能 | 代表场景 |
|---|---|---|---|---|
| 西皮 | 导板 | 散板,自由节奏 | 起调定场,抒发强烈情感 | 杨延昭登场时的悲愤控诉 |
| 西皮 | 原板 | 中速,一板一眼 | 叙述情节,表达理性诉求 | 杨延昭陈述潘洪罪状 |
| 西皮 | 快板 | 快速,有板无眼 | 情绪爆发,增强戏剧张力 | 公堂之上杨潘双方激烈对峙 |
| 二黄 | 慢板 | 缓慢,一板三眼 | 深沉抒情,展现内心复杂情绪 | 潘洪回忆罪行时的掩饰与恐惧 |
| 二黄 | 散板 | 散板,节奏自由 | 灵活收束,强化余韵 | 潘洪定罪后的绝望哀叹 |
《审潘洪》的曲谱在不同流派中呈现出多样化演绎,以老生行当为例,余派(余叔岩)讲究“脑后音”与“擞音”的运用,唱腔苍劲刚健,如杨延昭唱段中的“潘洪贼!”一句,通过高亢的脑后音与顿挫的节奏,突出人物的正义感;马派(马连良)则注重“巧腔”与“口语化”表达,唱腔流畅自然,更贴近生活化的人物状态;而奚派(奚啸伯)以“柔中见刚”为特色,在悲愤唱段中融入低回婉转的行腔,增强悲剧色彩,这些流派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唱腔旋律的细微变化上,更通过曲谱中的“气口”“装饰音”等标记得以传承,为京剧音乐的丰富性提供了生动例证。
作为传统京剧的经典剧目,《审潘洪》的曲谱凝聚了历代艺人的创作智慧,其程式化的声腔设计与灵活的情感表达,既体现了京剧“以简驭繁”的美学原则,也为现代京剧创作提供了宝贵借鉴,通过对曲谱的研习与演绎,不仅能深入理解京剧音乐的规律,更能感受到传统艺术中“忠奸分明”“惩恶扬善”的价值观传承,使这一经典剧目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FAQs

Q:《审潘洪》的曲谱主要采用哪些记谱方式?
A:《审潘洪》的传统曲谱以工尺谱为主,结合“板眼”符号(如“板”表示强拍,“眼”表示弱拍)和唱词记录,工尺谱用“上、尺、工、凡、六、五、乙”对应音高,通过符号标记节奏快慢(如“赠板”表示慢板,“流水板”表示快板),现代演出中,常在工尺谱基础上加入简谱或五线谱,方便年轻演员学习,同时保留传统板眼符号,确保声腔的规范性。
Q:不同流派演绎《审潘洪》时,曲谱处理的核心差异是什么?
A:核心差异在于“润腔”技巧与情感表达的侧重,例如余派唱腔注重“脑后音”与“擞音”,如杨延昭唱段中的“冤”字,通过脑后音拉长音高,再以擞音收尾,突出悲愤感;马派则强调“巧腔”,在“潘洪贼”一句中,通过“滑音”与“顿挫”的结合,使唱腔更具口语化张力;奚派则以“柔中见刚”为特色,在慢板唱段中融入“哭腔”,如“老夫年迈将何为”,通过低回婉转的行腔表现人物的无奈与苍凉,这些差异在曲谱中通过“装饰音”“气口”等细微标记得以体现,形成各流派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