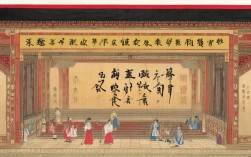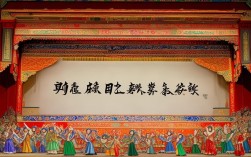豫剧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剧种,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一代代观众,而传统剧目《清风亭》更是其中以情感张力著称的经典,在这部讲述善恶因果、伦理撕裂的悲剧中,豫剧表演艺术家柏青的清唱艺术,以其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与独具韵味的唱腔技巧,为张元秀这一角色赋予了震撼人心的灵魂力量,成为豫剧舞台上难以复制的经典记忆。

《清风亭》的故事源于唐代传说,经历代戏曲艺人打磨,在豫剧舞台上形成了以“义养”为核心悲剧的叙事范式,剧情围绕贫苦老农张元秀夫妇拾得弃婴张继保展开,十三载含辛茹苦将养子抚养成人,却在生母以金银相诱时,张继保认亲而去,从此对养父母不闻不问,张元秀寻子至清风亭,却遭养子拒认,悲愤交加之下,夫妻二人双双撞亭柱而亡,全剧没有激烈的冲突场面,却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积累与人物情感的层层递进,将“恩将仇报”的人性悲剧撕开血淋淋的口子,而清唱段落正是人物情感爆发的关键节点——当张元秀在清风亭望着养子远去的背影,苍凉的唱腔如泣如诉,将十三年养育之苦、被弃之痛、绝望之恨凝聚于每一个音符,成为观众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在《清风亭》的众多演绎者中,柏青的版本之所以被誉为“巅峰之作”,核心在于她对“清唱”艺术的极致追求,柏青作为豫西调的代表人物,其嗓音兼具豫西调的苍劲醇厚与老旦行当的细腻真实,尤其擅长在无过多身段辅助的情况下,仅凭唱腔与眼神传递人物内心,在“寻子遇拒”的经典场次中,柏青饰演的张元秀从最初的满怀期盼到被拒后的如遭雷击,唱腔从平稳的“二八板”逐渐转为急促的“快二八”,再到悲怆的“哭腔”,她咬字如啮碎冰霜,“老天爷啊”的“天”字用“炸音”喷出,尾音却陡然下沉,仿佛一口鲜血哽在喉头;“你杀尽世人为何不杀我”的“我”字,以气声带过,配合眼神的空洞与身体的摇晃,将一个被至亲抛弃的老人的绝望演绎得入木三分,更难得的是,柏青的清唱并非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将生活细节融入表演:唱到“十三年为你熬瞎双眼”时,她会不自觉地揉搓双眼,手指因激动而颤抖,这些细微的动作让唱腔有了“肉感”,让观众仿佛能触摸到张元秀粗糙的手掌与破碎的心。
为更直观呈现柏青清唱的艺术特色,可将其与其他常见版本对比:

| 表演维度 | 柏青版特色 | 其他版本常见处理 |
|---|---|---|
| 唱腔设计 | 以豫西调“本腔”为基础,真假声转换自然,“悲音”贯穿始终,尾音多下沉收束,如“坠石入渊” | 多用“假声”高亢表现悲愤,尾音上扬,情绪外显 |
| 情感层次 | 从“期盼-失望-悲愤-绝望”递进,用“气声”“颤音”区分情绪层次,如“颤音”表现身体颤抖 | 情感爆发集中,多用“哭腔”直抒胸臆,层次感较弱 |
| 表演细节 | 配合唱腔加入“捶胸”“揉眼”“踉跄”等生活化动作,动作幅度小但力量感强 | 身段程式化,如“甩袖”“跺脚”等传统动作,与唱腔结合较松散 |
| 节奏处理 | 慢板“散板”结合,节奏自由灵活,根据情感需要调整字速,如“张继保”三字一字一顿 | 节奏规整,快慢板转换明显,情感表达更依赖唱腔本身 |
柏青在《清风亭》中的清唱艺术,不仅是豫剧“以情带声”美学的集中体现,更是传统戏曲现代化传承的典范,她没有固守老旦行当的程化表演,而是深入生活,将普通人的悲喜融入角色,让唱腔有了“烟火气”;她以豫西调为根基,在传统唱腔中融入个人理解,使《清风亭》这一古老剧目在当代观众中依然能引发强烈共鸣,当张元秀在清风亭的苍凉唱腔中缓缓倒下,观众听到的不仅是一个悲剧故事,更是对人性、伦理的深刻叩问,这正是柏青清唱艺术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问:柏青在《清风亭》中的清唱为何能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答:柏青的清唱艺术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情感共鸣,她严格遵循豫剧“字正腔圆”的演唱规范,豫西调的独特韵味让老戏迷感受到戏曲的本真;她通过生活化的细节处理(如颤抖的手指、空洞的眼神)将人物情感具象化,让年轻观众能直观感受到张元秀的绝望,打破年龄与时代的隔阂,实现“老戏新唱”的艺术效果。
问:《清风亭》中张元秀的清唱段落为何成为豫剧经典唱段?
答:这一唱段之所以经典,首先在于其与剧情的高度契合——清唱是张元秀情感爆发的顶点,十三年的压抑在这一刻释放,推动悲剧走向高潮;唱腔设计极具张力,从平稳到急促再到悲怆的节奏变化,配合“炸音”“气声”等技巧,将人物内心的撕裂感转化为听觉冲击;柏青的演绎赋予了唱段灵魂,她的表演让文字唱词有了温度,成为豫剧史上“声情并茂”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