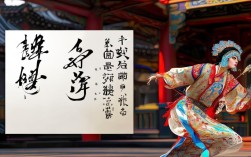独树戏曲作为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其艺术魅力不仅在于高亢的唱腔、生动的表演,更在于一种独特的叙事与抒情手法——“借赞子”。“借赞子”是独树戏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程式化表达,它以“借”为手段,以“赞”为核心,通过第三视角的介入、民间语言的智慧,将人物情感、剧情张力、地域文化巧妙融合,成为剧中点睛之笔,这一艺术形式不仅承载着地方文化的记忆,更展现了戏曲“虚实相生”的美学特质,为传统戏曲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独树戏曲起源于明清时期的河南南阳独树镇一带,这里地处伏牛山余脉,民俗文化深厚,民间说唱、歌舞与中原梆子戏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兼具山野豪情与市井烟火气的剧种,其唱腔以“独树调”为基础,融合了南阳大调曲子的婉转、豫西梆子的粗犷,形成了“高亢而不失细腻,豪放而富含韵律”的独特风格,而“借赞子”作为独树戏曲的标志性手法,最早可追溯至民间艺人的“即兴赞词”——在庙会、堂会演出时,为吸引观众,艺人在剧情关键处插入对人物、景物的即兴赞美,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程式,成为剧本创作与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功能上看,“借赞子”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串联剧情、塑造人物、传递情感的核心枢纽,其运用贯穿于独树戏曲的“起、承、转、合”之中。
“借赞子”的艺术特征首先体现在其“借”的智慧上,这里的“借”,既指借“人”之口,也指借“物”之象,更指借“境”之情,在传统剧目《花木兰》中,当木兰替父从军离家时,幕后会响起一段“借赞子”:“借阵风,送木兰,跨马提枪出家园;借明月,照征途,女儿心事向谁言?”此处借“风”“月”自然之物,既交代了行军场景,又以“风”的急切、“月”的清冷,烘托出木兰内心的不舍与决绝,实现了“景”与“情”的完美融合。“赞”为核心的表达,语言多采用民间俚语、谚语,韵律感极强,常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讲究押韵对仗,朗朗上口,如《包青天》中包公断案前的“借赞子”:“借惊堂木,震乾坤,明镜高悬照苍生;借乌纱帽,显正气,善恶到头终有报!”通过“惊堂木”“乌纱帽”等道具的象征意义,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塑造出包公威严正直的形象,同时传递出“正义必胜”的价值观。“借赞子”在表演形式上灵活多样,可由配角、幕后人员或演员本人分角演唱,甚至可通过集体帮腔增强气势,打破了戏曲“一人唱、众人听”的传统模式,形成了“台上台下互动、剧中剧外共鸣”的独特效果。
从功能层面看,“借赞子”在独树戏曲中承担着多重艺术使命,在叙事上,它如同“穿针引线”的线索,既能补充剧情背景,又能推动情节发展,白蛇传》中,白素贞水漫金山寺后,一段“借赞子”借“寺钟”“江潮”之象:“借寺钟,声声急,法海无情拆姻缘;借江潮,浪浪高,素贞情比天地宽!”短短数句,既交代了“水漫金山”的激烈冲突,又通过“钟急”“浪高”的意象对比,强化了白素贞对爱情的执着与法海的冷酷,使剧情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潮,在抒情上,它直抒胸臆,将人物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感外化,形成“以赞抒情”的感染力,如《秦香莲》中香莲寻夫无果时,借“寒鸦”“枯枝”之景:“借寒鸦,嗓喑哑,不如香莲唤夫家;借枯枝,摇风沙,世态炎凉似针扎!”以“寒鸦”的哀鸣、“枯枝”的萧瑟,将香莲的悲苦与绝望具象化,让观众在共鸣中体会人物的命运,在文化传承上,“借赞子”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语言中融入了大量南阳方言、民俗典故,如“借麦穗,金灿灿,农家汗水换丰年”“借牛车,慢悠悠,乡间小路话桑麻”,不仅展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印记,更让观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独树戏曲及“借赞子”的传承也面临挑战,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的疏离、方言传播的局限性、创新与传统的平衡问题,都使得这一古老艺术形式面临“失语”的风险,近年来,独树戏曲艺人尝试在保留“借赞子”核心韵律与叙事逻辑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题材与舞台技术,如在乡村振兴题材剧中,用“借赞子”赞“电商直播连山外,新农人把致富路来开”;在舞台表演中,结合多媒体技术,让“借赞子”中的“风”“月”“江潮”等意象通过光影效果具象化,增强了视觉冲击力,这些探索既守住了“借赞子”的“根”——民间语言的鲜活与情感的真实,又为其注入了“新”——与当代观众的审美共鸣,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 对比维度 | 借赞子 | 常见帮腔 | 旁白 |
|---|---|---|---|
| 主体视角 | 第三视角或旁观者,带有主观评价 | 多为群体视角,烘托气氛 | 客观叙述,推进剧情 |
| 语言风格 | 方言俚语,韵律感强,注重“赞”的情感 | 规范化唱词,侧重旋律 | 书面语或口语,平铺直叙 |
| 功能侧重 | 抒情、评价、象征 | 渲染气氛、强化情感 | 补充背景、交代情节 |
| 代表剧目 | 《花木兰》《包青天》 | 《梁祝》化蝶片段 | 《赵氏孤儿》背景叙述 |
FAQs
问:独树戏曲中的“借赞子”与戏曲中常见的“帮腔”有什么本质区别?
答: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视角与功能。“帮腔”多由后台群体演唱,侧重通过重复或强化唱词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感,视角较为客观,如《梁祝》中“化蝶”片段的帮腔,主要是为了增强浪漫色彩;而“借赞子”则更强调“借”的智慧,可由特定角色或旁观者演唱,视角灵活,既可抒情又可评价,语言更具个性化与地域性,如《包青天》中借“惊堂木”“乌纱帽”象征正义,功能上更侧重通过意象传递价值观,而非单纯烘托气氛。

问:在当代戏曲创新中,独树戏曲的“借赞子”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表达?
答:平衡的关键在于“守正创新”。“守正”即保留“借赞子”的核心内核——民间语言的鲜活、韵律的节奏感、以“借”抒情的叙事逻辑,如坚持使用南阳方言俚语,保持七字句、十字句的基本句式;“创新”则是在内容与形式上与时俱进,如将传统“借赞子”中的“风花雪月”替换为“高铁”“直播”等现代意象,在表演中融入灯光、多媒体技术让意象具象化,同时结合现代题材(如乡村振兴、抗疫故事)创作新“借赞子”,让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观众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避免“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