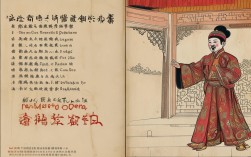京剧包飞是当代京剧舞台上备受瞩目的老生演员,他师承余派,是余派艺术的重要传承者与践行者,余派作为京剧老生行当的经典流派,由余叔岩在继承谭鑫培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创立,以“韵味醇厚、含蓄隽永、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著称,对后世京剧老生表演产生了深远影响,包飞深耕余派数十年,不仅在传统剧目的演绎中严格遵循余派精髓,更在当代舞台实践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余派传统与当代审美的关键人物。

余派的历史渊源与艺术精髓
要理解包飞的艺术归属,需先追溯余派的形成脉络,余派创始人余叔岩(1890-1943)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艺术根植于“老生三鼎甲”之一的谭鑫培(谭派),余叔岩幼年从吴联荪、谭鑫培(得其亲授)学艺,后吸收孙菊仙、汪桂芬、汪笑侬等流派的优点,结合自身嗓音条件与艺术感悟,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余派”,余派的艺术核心可概括为“唱念做打的全面精妙,尤以唱腔与念白见长”,其具体特征体现在多个维度:
在唱腔上,余派讲究“脑后音”“擞音”“擞连音”等技巧,行腔追求“刚而不躁、柔而不靡”,如《捉放曹》中“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的唱段,通过音色的浓淡变化与节奏的顿挫处理,将陈宫的惊恐、悔恨与无奈层层递进地展现;在念白上,余派强调“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无论是韵白还是散白,均注重字头的力度、字腹的饱满与字尾的收束,如《失空斩》中诸葛亮“忆昔当年在卧龙”的念白,沉稳中透着智慧,尽显军师气度;在做派上,余派主张“简练传神”,动作设计以少胜多,眼神、手势与身段高度统一,如《搜孤救孤》中程婴“白虎大堂领了命”的表演,通过微妙的表情变化与稳健的身姿,传递出角色的隐忍与坚韧;在剧目上,余派以“唱功戏”“做功戏”“靠把戏”并重,代表剧目包括《捉放曹》《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合称“失空斩”)、《搜孤救孤》《洪羊洞》《定军山》《阳平关》等,这些剧目至今仍是余派传承的基石。
余派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技巧的精湛,更在于其“以情带声、声情合一”的美学追求,余叔岩曾说:“唱戏要唱情,不能唱声。”这种将情感表达置于技巧之上的理念,成为余派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显著特征,也为后学者树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标准。
包飞的学艺历程与师承脉络
包飞1968年出生于北京梨园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1988年,他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师从余派名家王世续、李甫春、吴泽涛等,系统学习余派传统剧目,王世续作为余叔岩的入室弟子,深得余派真传,他要求包飞“先学规矩,再求变化”,强调对传统剧目的“死学活用”,在科班学习中,包飞每天坚持“喊嗓、吊嗓、练身段”,反复揣摩余派经典唱段的“气口”“劲头”与“韵味”,如《捉放曹》中“一轮明月照窗棂”的唱段,他通过数十遍的练习,逐渐掌握余派“擞音”的运用技巧,使唱腔既有“脑后音”的通透,又不失“哀而不伤”的情感克制。
毕业后,包飞加入北京京剧院,得到更多与余派前辈交流的机会,他曾向谭派传人王琴生请教《定军山》的“靠把功”,向言派传人张少楼学习《骂曹》的念白技巧,但这些学习始终围绕“余派核心”——即在尊重余派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在《失空斩》中,他借鉴了谭派“靠把老生”的身段稳健,同时保留余派诸葛亮“唱念做打”的细腻,使角色既有统帅的威严,又有儒将的温润。
多年的苦练与名师指点,使包飞逐渐形成“宗余而不泥余”的艺术风格,他常说:“余派是根,但不能只守着根,要让老树发新枝。”这种理念既体现在他对传统剧目的严谨传承上,也反映在他对余派艺术的当代诠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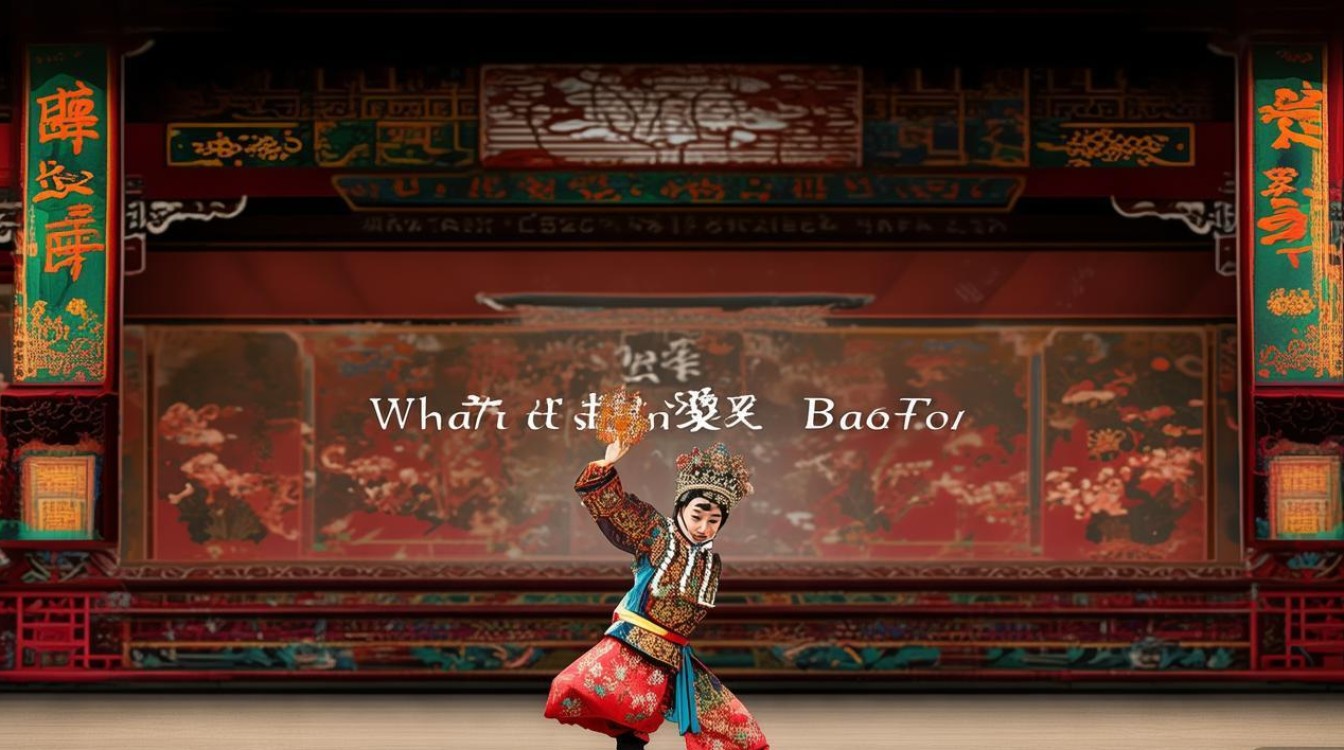
包飞的艺术实践与余派传承
作为余派传人,包飞的艺术实践始终围绕“传承”与“创新”展开,在传统剧目演绎中,他严格遵循余派的表演规范,力求“形似”与“神似”的统一,以《搜孤救孤》为例,该剧是余派“做功戏”的代表作,讲述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包飞在演绎程婴时,既保留了余派“唱念做打”的程式化处理——如“白虎大堂”一场的跪步、甩发、眼神交流,又通过细节的强化传递人物情感:当屠岸贾质问“孤儿下落”时,他通过喉头的微颤与眼神的躲闪,表现程婴的内心挣扎;当决定献子时,他通过缓慢的起身与坚定的眼神,展现角色的决绝,这种“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表演,正是余派“含蓄隽永”艺术风格的体现。
在舞台呈现上,包飞注重“整体感”,将唱、念、做、打融为有机整体,洪羊洞》中,他饰演的杨延昭已是暮年,唱腔上运用“衰音”表现人物的虚弱,身段上通过“颤步”“掩面”等动作凸显病态,念白上则放慢节奏,突出“力不从心”的疲惫,这种“唱念做打”的高度协调,使角色形象立体丰满,让观众感受到“余派艺术”的综合魅力。
包飞积极投身余派艺术的普及与教育,他多次参与“京剧进校园”“余派艺术讲座”等活动,通过现场教学、片段演示等方式,向年轻观众和演员讲解余派的历史与技巧,作为北京京剧院梅兰京胡剧团团长,他还组织创排了新编京剧《丝路长城》,在保留余派唱腔韵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音乐元素,探索传统京剧与当代审美的结合点,这些实践不仅扩大了余派艺术的影响力,也为流派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包飞对余派的创新与发展
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包飞并未囿于余派的既有范式,而是结合时代审美进行适度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的深度挖掘与舞台呈现的现代化处理两方面。
在人物塑造上,包飞注重“心理现实主义”,通过内心外化强化角色感染力,以《失空斩》为例,传统演绎中诸葛亮多侧重“智”的一面,而包飞则通过“唱念做打”的细节,展现其“人”的一面——如“空城计”一场,当司马懿大军压境时,他通过诸葛亮抚琴时“指尖的微颤”与“眼神的游移”,暗示角色内心的紧张,而非一味表现“从容”,这种“人性化”的处理,使经典角色更具现代共鸣。
在舞台呈现上,包飞在保留余派“简约美学”的基础上,适度运用现代技术,在新编京剧《丝路长城》中,他通过多媒体背景展现大漠风光,但唱腔设计仍严格遵循余派的“擞音”“脑后音”等技巧,做到“技术服务于艺术,不喧宾夺主”,这种“守正创新”的尝试,既尊重了余派的艺术传统,又适应了当代观众的观赏需求。

余派艺术核心特征与包飞实践对照表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包飞对余派的传承与创新,以下从艺术维度、余派特征、包飞实践三方面进行对照:
| 艺术维度 | 余派核心特征 | 包飞实践体现 |
|---|---|---|
| 唱腔 | 讲究“脑后音”“擞音”,行腔刚柔并济,以情带声 | 在《捉放曹》《失空斩》中,严格遵循余派“气口”与“劲头”,通过音色浓淡变化传递人物情感,如“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的唱段,既有“擞音”的细腻,又有“爆发力”的冲击 |
| 念白 | 字正腔圆,声情并茂,韵白与散白并重 | 在《搜孤救孤》《骂曹》中,注重字头的力度与字腹的饱满,如“白虎大堂领了命”的念白,沉稳中透着坚定,体现程婴的隐忍与曹操的霸气 |
| 做派 | 简练传神,眼神、手势、身段高度统一 | 在《洪羊洞》《定军山》中,通过“颤步”“甩发”“掩面”等动作,精准表现人物状态,如杨延昭的病态、黄忠的豪迈 |
| 剧目 | 以“唱功戏”“做功戏”“靠把戏”并重,代表剧目包括“失空斩”“搜孤救孤”等 | 严格传承《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等余派经典,同时尝试新编京剧《丝路长城》,在保留余派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 |
包飞代表剧目及余派风格体现表
包飞的代表剧目多为余派经典,以下列举其代表性角色及艺术特色:
| 剧目 | 角色 | 核心唱段/念白 | 艺术特色 |
|---|---|---|---|
| 《捉放曹》 | 陈宫 |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一轮明月照窗棂” | 唱腔运用“擞音”与“脑后音”,通过音色变化表现陈宫从惊恐到悔恨的情感转变;念白抑扬顿挫,体现人物的矛盾心理 |
| 《失空斩》 | 诸葛亮 |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忆昔当年在卧龙” | 唱腔苍劲有力,既有“老生”的沉稳,又有“军师”的智慧;做派注重“眼神”运用,通过眼神的转动展现人物的思考与决断 |
| 《搜孤救孤》 | 程婴 | “白虎大堂领了命”“手托孤儿心惨然” | 念白字字铿锵,体现程婴的坚毅;做派“以简驭繁”,通过“跪步”“掩面”等动作传递角色的悲痛与决绝 |
| 《洪羊洞》 | 杨延昭 | “将身儿来至在大营盘”“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 | 唱腔运用“衰音”,表现暮年病态;身段“颤而不乱”,凸显人物的虚弱与忧思 |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余派老生与其他流派(如马派、言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解答:余派、马派、言派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三大流派,其区别主要体现在艺术风格与表演侧重上,余派以“韵味醇厚、含蓄隽永”为特色,讲究“唱念做打的全面精妙”,尤重“以情带声”,代表人物余叔岩;马派(马连良)则风格“潇洒流畅、华丽明快”,念白“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做派“灵动飘逸”,强调“帅、脆、率”;言派(言菊朋)以“委婉细腻、跌宕多姿”著称,唱腔“多字腔”“擞连音”运用频繁,注重“字头、字腹、字尾”的细节处理,余派“重韵味”,马派“重潇洒”,言派“重细腻”,三者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京剧老生艺术的丰富面貌。
问题2:包飞在传承余派过程中,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解答:包飞对“传统与创新”的平衡可概括为“守正创新,以本求变”,所谓“守正”,即严格遵循余派的艺术规范,包括传统剧目的唱腔设计、念白处理、身段动作等,做到“不逾矩”;所谓“创新”,则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审美进行适度调整,如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心理现实主义”,在舞台呈现上适度运用现代技术,但创新始终以“不偏离余派精髓”为前提,在新编京剧《丝路长城》中,他保留了余派唱腔的“擞音”“脑后音”等核心技巧,同时通过多媒体背景增强故事的时代感,这种“技术服务于艺术”的创新,既传承了余派传统,又让老戏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