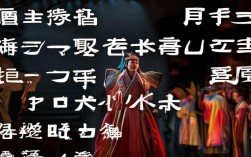戏曲舞台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集大成者,其独特的写意美学与程式化表演,让“以虚代实”成为核心创作逻辑,在表现骑马场景时,受限于舞台空间、表演成本、安全风险及艺术追求,戏曲从不使用真马,而是通过道具、身段、虚拟手法与音乐的多维融合,构建出一套“无马胜有马”的表演体系,这种替代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权宜之计,更是戏曲“神似高于形似”美学原则的集中体现,让马匹的动态、神韵与人物情感深度绑定,成为戏曲艺术的独特符号。

舞台限制与艺术追求:为何不用真马?
戏曲舞台方寸之间,既需承载复杂剧情,又要通过表演传递意境,真马的使用面临多重现实困境:舞台空间有限,真马难以完成转身、奔跑、腾跃等调度,且马粪、马尿等排泄物会破坏舞台卫生;真马训练成本高昂,需专人饲养、训练,且在锣鼓声嘈杂的舞台上易受惊,存在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戏曲艺术追求“虚实相生”,真马的“实”会限制观众的想象空间,而写意化的替代手段更能通过演员的表演引导观众“以意逆志”,实现“见鞭如见马,无马亦有马”的艺术效果,正如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所言:“戏曲之妙,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马鞭之用,正在此间。”
多维替代体系:从道具到表演的完整表达
戏曲中马匹的替代,并非单一手段的运用,而是道具、身段、虚拟手法与音乐的协同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马戏”表演语言。
道具替代:以小见大的符号象征
道具是马匹替代最直观的载体,其中马鞭是最核心的符号,马鞭的材质、长度、装饰均暗合人物身份与情境:武将常用竹制彩鞭,鞭尾缀红绸,如《长坂坡》中赵云的银枪配白缨鞭,凸显英武;文官则多用素色木鞭,如《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乌木鞭,体现儒雅;丑角则偏爱短小的“笑鞭”,鞭头系铃铛,行走时发出脆响,增添滑稽感,马鞭的“挥”“甩”“绕”“点”等动作,直接对应骑马时的“催马”“勒马”“转弯”“驻足”,如“甩鞭”表示马速加快,“绕鞭”表示马打盘旋,观众通过鞭的动作即可感知马的动态。
除马鞭外,马形道具在部分剧目中也有使用,如《昭君出塞》中的骆驼形道具(替代马匹,体现塞外场景)、《闹天宫》中的“马形灯”(用竹篾扎成马形,内置烛火,夜间表演时呈现剪影效果),这类道具虽具象,但仍保留写意色彩——骆驼道具仅保留驼峰与轮廓,马形灯则通过光影模糊细节,避免写实化破坏舞台整体意境。
身段表演:动态叙事的肢体语言
身段是演员用身体模拟马匹动态的核心手段,其中趟马是最经典的程式化表演,趟马时,演员双腿微屈,模拟骑马姿势,通过“扬鞭”“勒马”“加鞭”“趟马步”等动作,结合头部眼神、手臂幅度与脚步节奏,表现不同情境下的骑马状态:如《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趟马上场”,脚步轻快如飞,身躯挺拔,配合“急急风”锣鼓点,展现英姿飒爽的出征姿态;《三岔口》中任堂惠“夜行趟马”,脚步忽左忽右,身形低伏,配合“撕边”锣鼓,表现黑夜中摸索前行的紧张感。
圆场则是趟马的延伸,通过舞台调度中的圆周运动,表现马行路线与路途远近,演员根据情节调整圆场速度:缓行时步幅小、速度慢,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同窗出游的“慢圆场”;飞奔时步幅大、频率快,如《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骑马追击的“快圆场”,圆场的方向(顺时针/逆时针)也暗含情节:顺时针多表现前行,逆时针则表现折返或回望。

虚拟手法:虚实相生的意境营造
戏曲的“虚拟性”在马匹替代中体现得尤为极致,其核心是“以演员之‘意’,代观众之‘象’”,演员通过眼神、手势与步法的引导,让观众在想象中补全马的形态:如《西厢记》中张生骑马赴约,演员仅持鞭作“扬鞭”状,眼神望向前方,脚步轻快,观众便自然联想到“马蹄得得”的春日场景;《霸王别姬》中项羽被困垓下,演员勒马伫立,低头抚鞭,配合低沉的锣鼓,无需马匹即可传递出“英雄末路”的悲怆。
这种虚拟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演员的表演是“实”,观众的想象是“虚”,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匹意象,正如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所说:“戏曲的表演,就像画家的留白,演员的动作是笔触,观众的想象是意境,少了任何一方,画面都不完整。”
音乐与音效:听觉层面的氛围烘托
音乐是马匹替代的“隐形翅膀”,通过锣鼓、打击乐与乐器的配合,强化马的动态与情绪,锣鼓点是最直接的“马蹄声”:“急急风”表现马飞奔,如《挑滑车》中高宠追击金兀术,密集的“急急风”模拟马蹄雷鸣;“长锤”表现马缓行,如《游园惊梦》中杜丽春游园,舒缓的“长锤”配合脚步,体现悠闲心境;“马蹄点”则通过“仓才 仓才”的节奏变化,表现马的上坡、下坡或受惊。
乐器演奏同样不可或缺:唢呐的高亢表现骑马的豪迈,如《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挂帅”唱段前的唢呐独奏,伴随趟马动作,渲染巾帼英雄的气势;二胡的婉转表现骑马的忧伤,如《林冲夜奔》中林冲“夜奔”时的二胡曲,配合低沉的身段,传递落魄英雄的悲愤,音乐与表演的协同,让“马”的形象从视觉延伸至听觉,形成立体的艺术感染力。
替代方式的艺术特点对比
为更直观展现不同替代手段的侧重点,可归纳如下:
| 替代方式 | 具体形式 | 艺术特点 | 代表作品举例 |
|---|---|---|---|
| 道具 | 马鞭、马形道具 | 符号化、象征性强,侧重人物与马的互动 | 《长坂坡》(赵云白缨鞭) |
| 身段表演 | 趟马、圆场 | 程式化、动态叙事,侧重情节推进 | 《穆桂英挂帅》(趟马上场) |
| 虚拟手法 | 眼神、手势、步法引导 | 虚实相生,侧重意境营造与情感传递 | 《西厢记》(张生骑马赴约) |
| 音乐音效 | 锣鼓点、唢呐、二胡 | 听觉渲染,强化氛围与情绪 | 《林冲夜奔》(二胡伴奏) |
替代背后的文化密码
戏曲中马匹的替代,绝非简单的“无实物表演”,而是中国传统美学“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集中体现,它通过“以鞭代马”“以形写神”,让有限的舞台承载无限的想象,让演员的表演成为连接现实与艺术的桥梁,这种替代方式,不仅解决了舞台限制,更升华了戏曲的艺术表现力——马匹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人物情感的延伸、情节发展的催化剂,成为戏曲艺术“无中生有、以小见大”的经典范式,正如戏曲理论家张庚所言:“戏曲的魅力,在于它能让观众在‘无’中看到‘有’,在‘假’中感受‘真’,这种替代,正是戏曲艺术的最高智慧。”

FAQs
问:戏曲中的马鞭为什么能被观众接受为马的象征?
答:戏曲马鞭的象征意义源于长期的艺术约定俗成与观众的审美默契,马鞭的材质(竹、木)、长度(约1.2米)与装饰(彩绸、铜铃)与真马的马缰、鞭子形成视觉关联,让观众通过“相似性”建立联想;演员通过“扬鞭”“勒马”“绕鞭”等程式化动作,模拟骑马时的操控姿态,如“扬鞭”对应催马前行,“勒马”对应急停,这些动作经过百年传承,已成为观众熟悉的“马戏语言”;最重要的是,戏曲“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鼓励观众以想象填补舞台空白,马鞭成为“触发想象的开关”,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与鞭的动作,在脑中自动补全马的形态,最终形成“见鞭如见马”的艺术共识。
问:趟马动作中的“勒马”和“加鞭”分别传递了怎样的情感和情节信息?
答:“勒马”是趟马中的“制动”动作,演员通过身体后倾、马鞭后拉、脚步急停,配合眼神的凝重或回望,表现骑马时的紧急制动或观察状态,在《长坂坡》中,赵云怀抱阿阿在曹军中突围,突然“勒马”回望,配合“撕边”锣鼓与瞪圆的双眼,传递出对怀中婴儿的担忧与对敌情的警惕,情节上暗示“危机四伏”的转折;情感上则凸显赵云“忠义护主”的坚定。
“加鞭”则是趟马中的“加速”动作,演员通过马鞭快速前甩、身体前倾、步幅加大,配合密集的“急急风”锣鼓,表现催马急行的急切,在《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听到“辽国入侵”的消息,立即“加鞭”上场,配合挺拔的身姿与高亢的唢呐,传递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情节上推动“出征”高潮,情感上则凸显穆桂英“保家卫国”的责任感,这两个动作不仅是技巧展示,更是人物情感与情节发展的“动态符号”,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实现“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