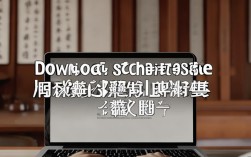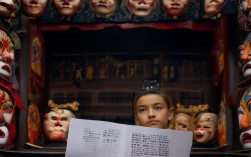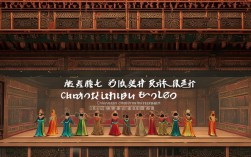戏曲毕业设计是对四年专业学习的一次全面检阅,从选题构思到最终呈现,每一步都凝聚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创新的探索,作为戏曲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设计选择了传统京剧《锁麟囊》的片段改编,结合现代舞台技术进行二度创作,整个过程既有对经典的深耕,也有对跨界融合的尝试,收获与挑战并存。

选题之初,我曾在“完全复刻传统”与“大胆创新突破”间犹豫。《锁麟囊》作为程派代表作,唱腔婉转跌宕,身段细腻繁复,其“仗义助人、贫贱不移”的主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最终决定以“传统为根,创新为翼”为原则,选取“春秋亭赠囊”这一核心场次,保留程派唱腔的精髓与薛湘玲的善良本性,同时通过多媒体投影与灯光设计,将“赠囊”时的心理活动外化,让古典故事更具当代审美张力,这一选择源于我对“戏曲如何活在当下”的思考——传统不是标本,而是需要通过时代语言重新激活的生命体。
剧本改编是毕业设计的第一个难点,原剧中“赠囊”情节通过唱词与动作推进,心理描写较为含蓄,为了让现代观众更易共情,我在保留【西皮流水】【二黄慢板】等核心唱段的基础上,增加了薛湘玲与薛夫人“临别赠言”的对话,通过细节铺垫其性格;在程派“脑后音”的“未开言来珠泪落”唱段后,插入一段无伴奏吟唱,用旋律的留白表现她看到富家女时“既羡慕又自持”的复杂心境,这一改编曾引发争议,有老师认为“破坏传统程式”,但经过反复请教与论证,最终确认“创新需以理解传统为前提”——吟唱虽是新形式,但其节奏与程派“抑扬顿挫”的韵律逻辑一致,是对传统音乐语言的延伸,而非颠覆。
排练过程则是对专业技能的极致打磨,我饰演薛湘玲,其“赠囊”后的“水袖功”与“圆场步”是重点,最初练习时,水袖总是“软而无力”,老师强调“水袖是手臂的延伸,需用肩带臂、臂带腕”,通过每日清晨的“抖袖、扬袖、翻袖”基本功训练,逐渐找到“力从脊发”的发力点;圆场步要求“快而不乱,稳而不僵”,为表现薛湘玲“匆匆离亭”的急切,我在传统“快步”基础上,调整步幅与身前倾角度,配合眼神的“先看囊再看人”,让动作既有程式美感,又传递出人物情绪,团队协作同样关键,灯光师为表现“雨打亭台”的意境,设计蓝白渐变光与雨滴投影,但初期投影与演员走位常错位,我们通过标记舞台点位、反复对光,最终实现“人景合一”的效果。

技术融合的尝试最具挑战性,也最让我体会到戏曲的包容性,在“赠囊”高潮处,我们用全息投影呈现薛湘玲回忆中“朱楼绣户”的场景:投影中的锦鲤随演员水袖翻飞而游动,花瓣随着唱腔节奏飘落,这一设计需要精确计算演员动作与投影内容的同步点,为此,我们采用“动作捕捉+实时渲染”技术,将演员的身段数据输入程序,让投影内容随表演动态变化,虽然调试过程耗时两周,但当第一次看到程派的“卧云”身段与投影中的云朵完美融合时,我深刻理解到“科技是工具,戏曲是灵魂”——技术若能服务于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就能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
毕业设计的完成,让我对“戏曲人”的身份有了更深的认知,它不仅是唱念做打的技艺传承,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我曾因唱腔气息不稳而沮丧,因团队意见不合而焦虑,但当舞台上掌声响起时,所有困难都化为成长的养分,这次设计让我明白,戏曲的未来,既需要“守得住根”——深耕传统程式与文化内涵,也需要“开新花”——以开放心态拥抱时代元素,让这门古老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继续流淌。
相关问答FAQs
Q1:戏曲毕业设计中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A1:平衡传统与创新的核心是“移步不换形”,传统是根基,需先吃透经典剧目的程式、美学与精神内核,如《锁麟囊》的程派唱腔、身段规范与“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创新则是表达手段,需围绕主题服务,如用现代技术强化情感共鸣、用新叙事结构优化节奏,但不能颠覆戏曲“写意”“虚拟”的本质,在改编中保留传统唱腔,仅通过灯光投影辅助叙事,既尊重传统,又让年轻观众更易理解。

Q2:毕业设计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的?
A2:最大困难是“跨专业协作的沟通壁垒”,我的团队包含灯光、多媒体、服装设计等多个专业同学,初期因戏曲术语(如“九龙口”“一桌二椅”)与设计专业术语(如“舞台分区”“视觉焦点”)不匹配,导致排练效率低下,解决方法是:建立“戏曲-设计术语对照表”,明确“追光突出主角”对应“舞台中心区聚焦”;排练前召开“分镜头会议”,用脚本标注每个环节的戏曲动作与设计效果的配合点(如“水袖翻飞时,投影同步飘落花瓣”),最终实现各部门对戏曲美学的共同理解,确保作品风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