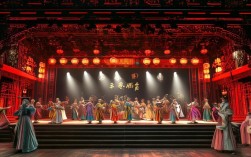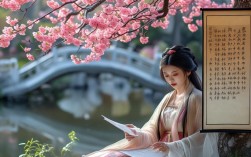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唱词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抒发情感的核心载体,而“风景”则是唱词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元素,戏曲唱词对风景的描摹,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现,而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将景、情、事、理熔于一炉,既构建出富有诗意的舞台空间,又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镜像与情感的催化剂,从昆曲的婉约雅致到京剧的豪迈大气,从地方戏的乡土气息到文戏的意境营造,唱风景的戏曲唱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动体现。

戏曲唱词中的风景描写,首先承担着“情景交融”的美学功能,古典诗词讲究“一切景语皆情语”,戏曲唱词沿袭并发展了这一传统,让景物成为人物情感的投射与延伸,如昆曲《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的唱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春日园林的“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形成强烈对比,明媚的景致反衬出杜丽娘深闺的孤寂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景物的“艳”与内心的“寂”交织,道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自由情感的朦胧渴望,再如《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崔莺莺的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秋日的“碧云”“黄花”“霜林”本已是萧瑟之景,加之“西风”“北雁”的动态烘托,更添凄清;而“离人泪”的设问,将景物与离愁彻底融合,秋景的每一笔都浸透着崔莺莺与张生分别时的心痛与不舍,景愈凄美,情愈深挚,这种“景中情、情中景”的写法,让风景不再是舞台的背景板,而是人物情感的“代言人”。
戏曲唱词中的风景描写具有“叙事时空构建”的作用,戏曲舞台的时空流动性极强,唱词通过描绘不同时节、地域的景物,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又推动了情节发展,如京剧《定军山》中老黄忠的唱段:“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到阵前,显威豪,贼战败,把阵逃,众儿郎,追赶了,重重叠叠上祁连山,旗幡招卷。”虽未直接写山景,但“祁连山”的意象与“旗幡招卷”的动态,既构建了战场的高远空间,又通过景物烘托出老黄忠老当益壮的豪迈气概,而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下凡时的唱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树上的鸟儿”“绿水青山”的明媚春景,不仅交代了七仙女下凡的时间(春日)与地点(人间田野),更以“带笑颜”的拟人化景物,反衬出天庭的压抑与人间的美好,为“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情节奠定了自由欢快的基调,许多戏曲通过“四季景”的轮转来叙事,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十八相送”一折,从“春则百花香”到“夏则荷花满塘”,再到“秋则桂子飘香”“冬则白雪茫茫”,四季景物的变化既是时间的流逝,也暗示了梁祝感情的升温与最终的悲剧结局,景物成为情节发展的“隐形线索”。
不同剧种因地域文化、音乐风格、表演形式的不同,唱风景的唱词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艺术个性,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唱词雅致,风景描写多具文人画的意境美,如《玉簪记·琴挑》中潘必正的唱词:“月明云淡露华浓,欹枕愁听四壁蛩,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以“月明”“云淡”“露华浓”的清冷夜景,烘托人物内心的孤寂与相思,语言如诗如画,意境空灵悠远,京剧则融合了南北文化,唱词的风景描写既有北方的雄浑,也有南方的婉约,如《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唱词:“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色近清明。”“碧落色近清明”的夜空,既交代了时间(深夜),又以“清明”的意象暗示了楚汉相争的结局(“清”暗指刘邦的汉军,“明”暗合“天命所归”),景物中蕴含着历史的苍凉,地方戏则更贴近乡土生活,风景描写充满泥土气息,如秦腔《三滴血》中李遇春的唱词:“猛抬头见一道蓝桥湾,湾里有船船无帆,叫船家快快把船渡,我过河去见爹颜。”“蓝桥湾”“船无帆”的乡土景物,真实再现了黄土高原的地理风貌,语言质朴直白,充满生活感,为更直观展现不同剧种风景描写的特点,可参考下表:

| 剧种 | 代表剧目 | 风景描写特点 | 经典唱词举例 |
|---|---|---|---|
| 昆曲 | 《牡丹亭·惊梦》 | 雅致含蓄,文人意境 |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颓垣” |
| 京剧 | 《霸王别姬》 | 雄浑苍凉,历史感厚重 | “猛抬头见碧落色近清明,云山万里,何日回归故里” |
| 越剧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婉约柔美,抒情性强 | “十八相送送呀送情意,但愿你记得我祝英台”中的“春则百花香,夏则荷花满塘” |
| 黄梅戏 | 《天仙配》 | 田园清新,生活气息浓郁 | “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 |
| 川剧 | 《柳荫记》 | 乡土灵动,语言活泼 | “远看青山一座座,近看绿水绕山坡” |
戏曲唱词中风景描写的艺术手法,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其一,意象的象征性,如“梅兰竹菊”象征品格,“杨柳”象征离别,“月亮”象征团圆或思念,这些意象在唱词中反复出现,形成约定俗成的文化密码,如京剧《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唱词:“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以“冰轮”“皓月”象征杨玉环的绝代风华与内心的孤寂,意象与人物完美融合,其二,修辞的丰富性,对仗、比喻、拟人、叠字等手法运用自如,增强唱词的韵律美与画面感,如《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设问,“泪染霜林”比喻新奇;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以花喻人,拟人手法让景物充满情感张力,其三,虚实结合,既写实景,又写虚境,如《牡丹亭》中的“游园”一折,“姹紫嫣红”是实景,“断井颓垣”既是实景(深闺荒园),又是虚景(杜丽娘内心的荒芜),虚实相生,拓展了唱词的意境空间。
戏曲唱词中的风景描写,是“景、情、事、理”的高度统一,它不仅构建了戏曲舞台的诗意空间,更成为人物情感的外化、叙事的载体与文化的符号,从文人雅士的园林小景到乡野村夫的田园风光,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山河到儿女情长的离愁别绪,唱风景的戏曲唱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些唱词穿越数百年时光,至今仍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情感纽带。
FAQs

Q1:戏曲唱词中的风景描写与诗词中的写景有何异同?
A:相同点在于都强调“情景交融”,通过景物抒发情感,追求意境美;不同点在于,戏曲唱词需服务于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需与表演、音乐结合,具有更强的戏剧性,而诗词写景更侧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与艺术形式的独立,同写“秋景”,《西厢记·长亭送别》的“碧云天,黄花地”需结合崔莺莺的离愁与剧情转折,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则更侧重文人自身的羁旅之思。
Q2:为什么传统戏曲中常以“四季”“山水”等自然景物作为唱词素材?
A:“四季”“山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象,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生命、宇宙的哲学思考,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序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这些意象易引发观众共鸣;戏曲舞台的时空限制需要通过景物意象来暗示,如“四季景”可表现时间流逝,“山水景”可构建空间场景,既经济又富有诗意,符合戏曲“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