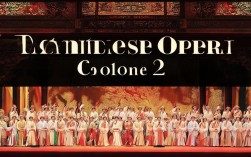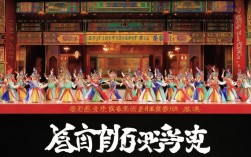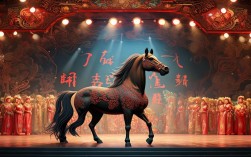京剧《乌盆记》是中国传统戏曲宝库中的经典公案剧,以“冤魂伸雪”为核心主题,融合伦理批判、民间信仰与艺术审美,自清代以来久演不衰,其故事改编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第七回至第十一回,经京剧艺人不断加工,成为展现京剧唱、念、做、打综合艺术的重要载体,剧中“清官断案”与“冤魂诉冤”的双线叙事,既满足了民间对正义的向往,也彰显了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剧情:冤魂寄乌盆,清官雪奇冤
《乌盆记》的故事围绕商人刘世昌的被害与伸冤展开,剧情可分为四个阶段:
| 剧情阶段 | 主要情节 | 关键人物 |
|---|---|---|
| 开端:客途遇害 | 殷商刘世昌经商归乡,途遇窑户赵大,借宿其家,赵大见财起意,与妻子合谋将刘世昌杀害,焚尸灭迹,用骨灰和泥制成乌盆。 | 刘世昌、赵大夫妇 |
| 发展:魂盆诉冤 | 穷苦老人张别古向赵大讨要乌盆,不料乌盆竟在夜间显灵,发出哭声并诉说冤情,张别古吓得魂飞魄散,得知刘世昌魂魄寄身乌盆,盼为其伸冤。 | 张别古、刘世昌(魂) |
| 高潮:包公断案 | 张别古带着乌盆前往开封府击鼓鸣冤,包拯初时不信,乌盆却当堂“说话”,控诉赵大夫妇的罪行,包拯敏锐察觉案件蹊跷,设计传唤赵大夫妇。 | 包拯、张别古、赵大夫妇 |
| 结局:惩凶雪冤 | 包拯以智谋迫使赵大夫妇认罪,交代杀害刘世昌的经过,刘世昌冤情得雪,魂灵安息,赵大夫妇受到严惩。 | 包拯、刘世昌(魂)、赵大夫妇 |
全剧通过“被害—显灵—告状—断案”的递进式情节,将冤屈的沉重、正义的彰显与民间对清官的崇拜融为一体,节奏紧凑,扣人心弦。
人物形象:善恶分明,性格鲜明
剧中人物塑造极具典型性,正邪对立鲜明,个性突出:

| 人物 | 身份 | 性格特征 | 舞台形象 |
|---|---|---|---|
| 刘世昌 | 富商 | 正直、善良,遭遇横祸却魂不屈 | 青衣扮相,唱腔悲凉凄楚,魂魄显灵时身形飘忽,眼神含冤 |
| 包拯 | 开封府尹 | 刚正不阿、睿智机敏,明察秋毫 | 黑脸铜锤花脸,唱腔沉稳威严,动作利落,目光如炬 |
| 赵大 | 窑户 | 贪婪凶残、胆小自私,见利忘义 | 丑角扮相,表演夸张,言语粗鄙,做功突出其心虚与狡黠 |
| 张别古 | 穷苦老人 | 善良正直、胆大细心,怜悯冤魂 | 老生扮相,念白朴实,步履蹒跚,情感真挚 |
包拯的“清官”形象与刘世昌的“冤魂”形象形成强烈对比,前者代表世俗的正义力量,后者则寄托了民间对“善恶有报”的朴素信仰,而赵大夫妇的恶行则成为批判人性贪婪的典型。
艺术特色:唱念做打,尽显功力
《乌盆记》作为京剧传统戏,在艺术表现上充分展现了京剧的综合魅力:
| 艺术元素 | 具体表现 | 艺术效果 |
|---|---|---|
| 唱腔 | 刘世昌“反二黄”唱段《未曾开言泪双流》,节奏缓慢,旋律低回婉转,如泣如诉;包拯“西皮流水”唱段,明快有力,展现其威严与睿智 | 刘世昌唱腔强化悲情氛围,包拯唱腔凸显人物气场 |
| 表演 | 魂盆显灵一场,演员通过眼神、手势模拟“乌盆说话”,配合身段的飘忽,营造出神秘恐怖的氛围;赵大夫妇受审时的做功,通过跪步、抖袖等动作表现其惊慌失措 | 虚实结合,增强戏剧张力,人物心理刻画入木三分 |
| 舞台美术 | 乌盆道具以陶土烧制,表面涂黑,盆底刻“冤”字,简洁而寓意深刻;公堂场景采用一桌二椅的象征性布景,突出京剧“以虚代实”的美学特征 | 道具与布景服务于剧情,强化“冤案”主题,引导观众沉浸 |
传承与影响
《乌盆记》自清代形成以来,历经谭鑫培、马连良、裘盛戎等京剧名角的演绎,乌盆告状”“包公审案”等折子戏成为经典,剧中“清官文化”与“冤魂叙事”契合传统伦理观念,至今仍是舞台上的常演剧目,甚至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跨越时代,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于精彩的剧情,更在于通过京剧特有的艺术语言,传递了“正义必胜”的永恒主题。

相关问答FAQs
Q1: 《乌盆记》中的“乌盆”在戏曲中是如何实现“显灵”效果的?
A1: 舞台上“乌盆显灵”主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技巧和舞台调度实现,演员手持乌盆,通过眼神的凝视与闪烁、手部的细微颤抖模拟“乌盆说话”,配合低沉的配音(幕后或特殊音效)营造神秘感,演员的身段会做出飘忽、停顿等动作,暗示魂魄附体,再结合灯光的明暗变化(如突然变暗或聚焦乌盆),让观众在虚实结合的表演中感受到“显灵”的戏剧效果,这是京剧“虚拟性”与“程式化”的典型体现。
Q2: 为什么《乌盆记》能成为京剧经典公案戏的代表?
A2: 其经典地位源于三方面:一是主题深刻,通过“冤魂伸冤”的故事,既满足了民间对正义的朴素追求,也暗含对人性贪婪的批判,具有普遍的伦理共鸣;二是艺术精湛,唱腔上融合“反二黄”“西皮”等板式,表演上兼顾文戏的细腻与武戏的张力,集中展现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魅力;三是人物典型,包拯的清官形象、刘世昌的冤魂形象、赵大的恶徒形象,均成为戏曲人物塑造的范本,历经百年传承仍具生命力,因此成为公案戏中的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