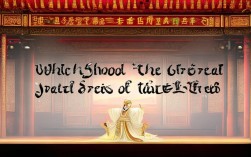河南豫剧《打銮驾》作为传统经典剧目,以其跌宕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塑造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豫剧舞台上久演不衰,而李斯忠先生的演绎更是为这出戏注入了灵魂,成为豫剧黑头行当的标杆之作,李斯忠(1921-1988)是河南豫剧史上著名的黑头演员,工铜锤花脸,以嗓音宏亮、行腔刚健、表演质朴著称,被誉为“河南第一黑头”,他深得豫剧传统精髓,又注重人物内心刻画,将花脸艺术的“唱、念、做、打”融会贯通,尤其在《打銮驾》中饰演的包拯,既展现了铁面无私的威严,又传递出为民请命的赤诚,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打銮驾》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宋代,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回京途中遭遇庞妃的銮驾阻路,庞妃仗着兄长太师庞吉的权势,不仅不避让圣旨钦差,反而命人刁难包拯,甚至欲加害之,包拯怒不可遏,不顾銮驾的皇家威仪,依法惩治庞妃的随从,怒打銮驾,维护了国法尊严,彰显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全剧冲突集中,从“路遇銮驾”的试探,到“据理力争”的交锋,再到“怒打銮驾”的高潮,层层递进,将包拯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斯忠在剧中对包拯的塑造,堪称“一人千面”的典范,他的唱腔以豫剧传统【二八板】【快二八】为基础,结合黑头特有的“脑后音”“炸音”,形成一种浑厚如钟、高亢裂帛的声腔特点,在“包拯陈州去放粮”的核心唱段中,他运用“起腔”“垛板”“送板”等多种板式,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虚实变化,既表现了包拯体恤民情的忧思,又暗含了对庞氏专权的愤懑,銮驾挡路心恼恨”一句,他先以低沉的“脑后音”铺垫,字字铿锵,到“恼恨”二字突然拔高,用炸音爆发,将包拯的怒火与压抑交织的情绪推向顶点,念白方面,他摒弃了花脸行当常见的“瓮声瓮气”,而是以清晰的“韵白”结合刚劲的“京白”,如面对庞妃侍卫的呵斥,他眼神一凛,声如洪钟:“大胆!钦差在此,还不速速回避!”短短一句,既有官员的威仪,又有执法者的凛然,令人不敢直视。
表演上,李斯忠注重“神形兼备”,他虽以唱功见长,但身段、台步同样精准,剧中“打銮驾”一场,他左手托髯,右手握袖,面对象征皇权的銮驾,先是昂首挺立,眼神如电,展现“不惧天威”的胆魄;随后挥袖怒打,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配合铿锵的锣鼓点,既有程式化的美感,又充满真实的力量感,他通过眼神的细微变化——从最初的克制、隐忍,到交锋时的愤怒、坚定,再到打銮驾时的决绝、悲壮,将包拯“外冷内热”的复杂内心外化于舞台,让观众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威严也有温度的“包青天”。

李斯忠的《打銮驾》不仅是个人的艺术巅峰,更推动了豫剧黑头行当的发展,他将传统花脸的“架子功”与铜锤花脸的“唱功”深度融合,打破了豫剧黑头“重唱轻做”的局限,形成了“以声塑形、以形传神”的表演风格,该剧也成为豫剧教学中的经典剧目,其唱腔、念白、身段被作为范本传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演员,虽时隔多年,但李斯忠在《打銮驾》中塑造的包拯形象,依然通过录音、录像资料留存,成为豫剧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经典表演片段与艺术特点分析
| 表演片段 | 艺术特点 | 情感表达 |
|---|---|---|
| “包拯陈州去放粮”唱段 | 以【二八板】为主,脑后音与炸音结合,字头咬紧,字腹饱满,尾音下沉 | 表现包拯忧国忧民、体恤百姓的赤子之心,暗含对朝政腐败的愤懑 |
| “銮驾挡路”对峙 | 韵白与京白结合,声调抑扬顿挫,眼神如电,配合顿足、甩髯等身段 | 展现包拯面对权贵时的不卑不亢,以及“法理大于皇权”的坚定立场 |
| “怒打銮驾”高潮 | 台步稳健有力,挥袖动作刚劲,配合快节奏锣鼓,动作幅度大但不失程式美 | 释放包拯对庞氏专权的怒火,彰显“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刚正品格 |
相关问答FAQs
Q1:李斯忠在《打銮驾》中塑造的包拯形象,与其他流派的包公有何不同?
A1:李斯忠塑造的包拯更侧重“刚正中的悲悯”,他区别于京剧包公的“架子花脸”风格,以豫剧铜锤花脸的“唱功”为核心,用声腔的“刚”与“柔”对比——面对百姓时,唱腔低沉婉转,流露体恤之情;面对权贵时,声如洪钟,迸发雷霆之怒,他的表演更贴近河南民间语言的质朴,念白中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让“包青天”的形象更具生活感和亲切感,而非高高在上的“神”。
Q2:《打銮驾》为何能成为豫剧经典剧目?其现实意义是什么?
A2:《打銮驾》的经典性源于“剧情冲突激烈”与“人物精神永恒”,全剧围绕“法与权”的矛盾展开,情节紧凑,矛盾集中,符合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审美要求;包拯“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精神,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法治文化与正义精神的象征,在当代,该剧依然警示着权力需要监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意义,因此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