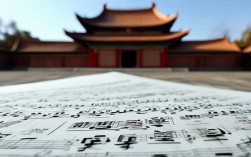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以其程式化的表演、写意的舞台呈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在众多京剧表演程式中,“摆驾”是极具特色的出行类程式,主要用于表现帝王、后妃或高级官员的出行场景,它并非简单的动作模仿,而是融合了古代礼制、舞蹈美学、音乐节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表达,既精准传递了角色的身份地位,又推动了剧情发展,更成为观众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摆驾”一词,本义为帝王出行前整理仪仗、启驾的过程。“摆”有排列、整理之意,“驾”指帝王的车驾与仪仗,在古代宫廷,帝王出行需经过“清道”“整驾”“卤簿陈列”等复杂礼仪,《后汉书·舆服志》便记载了天子出行的“大驾”仪仗规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前有“导骑”,后有“殿骑”,旌旗蔽日,鼓乐震天,京剧将这一现实场景提炼、简化,通过程式化的舞台动作进行艺术再现,清代宫廷戏曲已有此类表演,后经京剧前辈艺人的打磨,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表演范式,成为区分角色等级、烘托场合氛围的重要手段。
京剧“摆驾”的表演,是一套包含动作、队形、音乐、道具的完整程式,其核心在于“以形传神”,通过外在动作展现角色的内在身份与情感,具体而言,其表演要素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动作设计:以“整冠”“甩袖”“抬步”“转身”为核心动作,帝王“摆驾”时,多先以“正冠”动作展现威严,双手微抬整理冠缨,再以“甩袖”配合步伐——左袖轻甩,右脚迈出,步幅沉稳,每步约一尺,称“方步”;后妃“摆驾”则动作柔美,以“兰花手”提宫灯或执拂尘,碎步前行,称“莲步”;官员“摆驾”动作简洁,双手端带或执笏,步伐紧凑,体现其干练身份。
队形排列:以“龙套”为核心角色,通过站位变化表现仪仗规模,帝王“大摆驾”时,龙套分两列排开,每列4-8人,手执“回避”“肃静”牌、金瓜、钺斧等仪仗道具,呈“八字形”随角色前行;亲王“摆驾”则龙套减至4人,分列两侧;后妃出行以“宫女”“太监”替代龙套,手执宫灯、团扇,呈“一字形”跟随,体现宫廷生活的精致。
音乐配合:以锣鼓经与管弦乐烘托氛围,帝王“摆驾”常用“急急风”开场,鼓点密集如马蹄声,继以“九锤半”过渡,最后唢呐吹奏“朝天子”,旋律庄重威严;后妃“摆驾”则用“小锣抽头”起奏,配以“南梆子”唱段,旋律婉转柔和;官员“摆驾”多配“长锤”,节奏明快,体现其行事的效率。

道具运用:道具是身份的直观象征,帝王“摆驾”必用“銮驾”道具,包括华盖、龙旗、宫扇等,华盖由太监高举,随角色移动而晃动,象征“皇权如日”;后妃“摆驾”多用“宫灯”“拂尘”“香囊”,道具小巧精致,凸显女性特质;官员“摆驾”则以“印盒”“签筒”“水火棍”为主,体现其职权范围。
根据场合规模与角色身份,“摆驾”可分为“大摆驾”与“小摆驾”两类,二者在细节上差异显著:
- 大摆驾:用于登基、祭天、巡游等重大礼仪,规模宏大,仪式感强,如《打龙袍》中李后(李妃)复位后的“大摆驾”,龙套8人分列两侧,手举“金瓜”“钺斧”,李后身着凤冠霞帔,在“四击头”锣鼓中缓步登台,先“整冠”,再“甩袖”,最后抬手示意“起驾”,动作幅度大,眼神威严,通过仪仗的密集排列与音乐的庄重,展现其“母仪天下”的身份。
- 小摆驾:用于日常出行、省亲、小范围巡游等场景,规模精简,生活化气息浓,如《贵妃醉酒》中杨贵妃“摆驾”百花亭,仅2名宫女提宫灯、1名太监执拂随行,杨贵妃身着云肩,以“碎步”前行,配合“南梆子”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动作轻柔,眼神含情,将贵妃出行时的闲适与期待融入其中,无大摆驾的威严,却更具女性柔美。
“摆驾”在京剧剧情中绝非简单的“走过场”,而是承担着多重叙事功能:
身份标识:通过仪仗规模、动作特点、音乐节奏,快速向观众传递角色身份,如《霸王别姬》中项羽兵败垓下后“摆驾”回营,虽为帝王,但动作沉重,龙套仅4人,锣鼓急促(用“乱锤”),暗示其霸业将倾的悲壮;而《龙凤呈祥》中刘备招亲时的“摆驾”,龙套6人,动作轻快,音乐喜庆(用“小锣花梆子”),既展现其皇叔身份,又铺垫“甘露寺相亲”的轻松氛围。
情感外化:动作细节可折射角色内心,如《贵妃醉酒》中杨贵妃“摆驾”至百花亭,见高力士未备酒菜,眼神由期待转为失落,提宫灯的手微微颤抖,碎步放缓,通过动作的微妙变化,将“失宠”的郁结情绪外化,无需台词便让观众共情。

场景转换:作为“转场程式”,推动剧情发展,如《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康熙“摆驾”微服下江南,通过“整冠—甩袖—挥手—登车”一套连贯动作,完成从“帝王”到“平民”的身份转换,既交代出行背景,又自然引出后续“民间查案”的剧情。
经典剧目中的“摆驾”表演,堪称程式与剧情完美结合的范例,以《穆桂英挂帅》中“朝廷点将”一幕为例:宋王“摆驾”校场,龙套8人手举“龙旗”“凤旗”,宋王身着龙袍,在“九锤半”锣鼓中登台,先“正冠”彰显威严,再抬手示意“平身”,动作舒展,眼神坚定;穆桂英“接驾”时,先“跪拜”,再“起身”,步伐利落,眼神坚毅,通过“宋王摆驾”的庄重与“穆桂英接驾”的英武,既展现“君臣之礼”,又凸显穆桂英“巾帼不让须眉”的性格,为后续“挂帅出征”埋下伏笔。
相关问答FAQs
问:京剧中的“摆驾”和“起霸”有什么区别?
答:“摆驾”与“起霸”同属京剧程式,但功能与表演重点截然不同。“摆驾”是“出行程式”,用于表现角色出行场景,侧重仪仗排列与行进动作,如帝王乘车驾、官员列队出行,动作舒缓,强调身份展示,音乐以唢呐、锣鼓的庄重为主;“起霸”则是“整武程式”,用于表现武将上阵前的整装仪式,侧重披挂铠甲、调整兵器的英武姿态,如《长坂坡》赵云的“起霸”,动作刚劲有力(如“踢腿”“亮相”),锣鼓急促(用“急急风”),突出将帅威风,简言之,“摆驾”是“行走的身份”,“起霸”是“静止的威严”。
问:为什么京剧中的“摆驾”仪仗规模会因角色不同而变化?
答:这源于古代礼制中的“等差秩序”,京剧通过程式化表演将其艺术化体现,古代《周礼》便规定“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等级森严,京剧将这一制度转化为舞台语言:皇帝“摆驾”用8名以上龙套,象征“九五之尊”;亲王、郡王等皇室成员减至4-6人,体现“尊卑有序”;后妃出行无龙套,仅配宫女、太监,符合“男尊女卑”的礼制;官员则按品级,三品以上可用“回避”“肃静”牌,以下则简化,甚至无仪仗,这种规模差异,既是对历史礼制的艺术化再现,也帮助观众快速识别角色身份,强化舞台的叙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