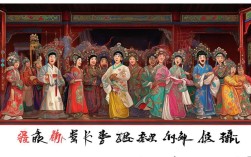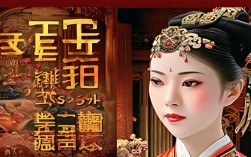在豫剧的百花园中,以村官为主角的作品始终扎根乡土、贴近民心,而“李夭成”这一形象更是凭借其真实感与时代感,成为近年来豫剧舞台上闪耀的基层干部典型,他并非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带着泥土气息的“身边人”——可能是返乡的大学生,可能是本地的致富带头人,更可能是在乡村振兴浪潮中摸爬滚打的普通村干部,豫剧以其特有的高亢唱腔、生活化的念白和生动的舞台表现,将李夭成“为村民办实事、带领大家共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既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变迁,也刻画了新时代村官的责任与担当。

李夭成的故事,往往从“接烫手山芋”开始,许多剧目中,他上任时面对的是一个“空心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土地撂荒,产业凋敝,邻里矛盾积重难返,比如某经典剧目中,他刚到村口,就遇到村民因灌溉水渠问题争吵不休,老支书拍着大腿说“夭成啊,这村官可不是人干的活!”可李夭成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白天顶着烈日走家串户,晚上在煤油灯下记民情日记,用三个月时间跑遍了全村23个村民小组,手绘出“民情地图”,标出哪家孩子上学难、哪户老人看病远、哪片地缺水源,这种“脚上沾泥、心中有数”的务实作风,很快让村民从“质疑”变为“信任”。
发展产业是李夭成工作的“重头戏”,面对“守着金饭碗没饭吃”的困境,他拒绝“拍脑袋决策”,而是带着村里的能人外出考察,结合本地气候和土壤特点,最终确定发展“高山有机蔬菜”,但村民不买账:“种了一辈子玉米,突然改种菜,谁敢担风险?”李夭成没有强迫,而是带头承包了30亩试验田,自掏腰包买种子、请技术员,白天在地里除草施肥,晚上挨家挨户算“经济账”——“一亩玉米最多赚1000块,一亩有机蔬菜能卖8000块,咱这山高水好,不种菜太亏了!”那年冬天,第一茬蔬菜丰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城市,村民每亩增收6000多元,这下大家彻底服了,第二年,全村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500亩,还成立了合作社,李夭成被大家推选为合作社理事长,他说:“我不是什么能人,我就是想让大伙的腰包鼓起来!”
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是李夭成另一项“硬功夫”,农村工作千头万绪,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往往因“鸡毛蒜皮”而起,某剧中,村民王老二和李老汉因宅基地边界问题积怨十年,甚至动手打架,谁劝都不管用,李夭成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把两人请到村委会,泡上茶,先听他们“倒苦水”,再讲“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最后拿出老宅地契,当着大家的面重新丈量,他指着地契说:“咱祖辈都是乡里乡亲,为了几尺地伤了和气,对得起先人吗?”说着说着,两个大男人红了脸,当场握手言和,事后,李夭成还组织村民制定了《村规民约》,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形式,让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村里老人说:“以前有事找干部,总觉得‘门难进、脸难看’,现在找李书记,他就像咱自家人,端茶倒水,掏心窝子说话!”

为了让乡村留住“根”,李夭成特别注重文化传承,他深知,乡村振兴不能只看“钱袋子”,更要看“精气神”,他组织村里的老艺人成立豫剧小分队,把村里的故事编成戏词——蔬菜致富记”“邻里一家亲”,在农闲时搭台演出,村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他修复了村里的老祠堂,建起了“农家书屋”,孩子们放学后能来看书,老人能来下棋;他还邀请返乡青年设计文创产品,把豫剧脸谱、剪纸元素印在包装上,让蔬菜合作社的产品有了“文化附加值”,有年轻人问他:“书记,现在都啥年代了,还搞这些老古董干啥?”李夭成笑着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丢不得!有了文化,咱村才有魂,年轻人才愿意回来!”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李夭成的工作成效,以下通过表格归纳其典型事迹与成果:
| 工作领域 | 具体举措 | 取得成效 |
|---|---|---|
| 民情调研 | 三个月走访23个村民小组,绘制“民情地图” | 掌握全村一手民情,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
| 产业发展 | 带头试种高山有机蔬菜,成立合作社 | 村民蔬菜亩均增收6000元,年产值超500万元 |
| 矛盾调解 | 创新“老支书调解室”“村规民约”机制 | 十年积怨邻里矛盾化解率达95%,获评“无讼村” |
| 文化振兴 | 组建豫剧小分队,修复老祠堂,建农家书屋 | 村剧团获市级“优秀民间文艺团队”,返乡青年增加30人 |
李夭成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豫剧用“生活流”的笔触,让他脱离了“符号化”的标签,他会在村民不理解时“红脸出汗”,会在产业遇到挫折时“偷偷抹泪”,也会在村民丰收时“笑得像个孩子”,这种真实感,让观众看到了基层干部的“不容易”,更看到了他们的“傻劲儿”——傻傻地相信“只要肯干,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傻傻地坚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初心,正如豫剧唱词中所唱:“一身泥土两脚霜,心里装着百姓粮;不求官帽有多大,但求乡亲笑开颜。”这正是李夭成这一形象的灵魂所在,也是豫剧作为“乡土艺术”最珍贵的温度。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豫剧《村官李夭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吗?
解答:是的,豫剧《村官李夭成》的创作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其原型多取材于河南本土的优秀村官事迹,如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的“领头雁”、扎根基层解决民生难题的“实干家”,编剧团队曾深入多地乡村采风,记录下村官们“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的真实工作状态,以及村民从“观望”到“参与”的转变过程,例如剧中“试种蔬菜”的情节,就参考了河南某村村官带领村民从传统种植转向有机农业,最终实现增收的真实案例,李夭成的形象既有艺术加工,更有现实底色,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身边人”的影子,产生强烈共鸣。
问题2:豫剧如何通过舞台表现展现李夭成的“基层感”?
解答:豫剧通过多种舞台手段强化李夭成的“基层感”,让观众仿佛置身乡村,一是语言上,大量使用河南方言俚语,如“中”“恁”“得劲儿”等,以及“庄稼话”(如“种地靠的是‘粪’,不是‘劲’”),让人物语言接地气;二是道具上,锄头、草帽、账本、民情日记等“乡土物件”频繁出现,甚至有村民手拿烟袋、坐在马扎上对话的场景,还原乡村生活场景;三是表演上,演员借鉴了“地摊戏”的质朴风格,没有过多华丽的程式化动作,而是通过“蹲在地里拔草”“蹲在村民家炕头唠嗑”等细节,塑造出“泥腿子干部”的形象;四是唱腔上,以豫剧“祥符调”“豫东调”为基础,融入哭腔、垛板等表现手法,如在村民不理解时用低沉的唱腔抒发委屈,在产业丰收时用高亢的“欢腔”表达喜悦,让人物情感与豫剧韵味完美融合,这些手法共同作用,让李夭成这个角色“立”在了舞台上,也“活”在了观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