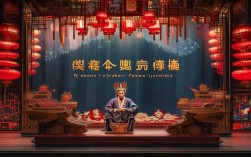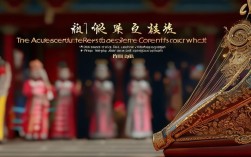京剧《杨家将》中的《碰碑》一折,是展现杨继业忠勇悲壮的经典剧目,其伴奏作为京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乐器的精妙组合、旋律的跌宕起伏,与表演、唱腔共同构建出苍凉悲怆的艺术氛围,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的关键力量,京剧伴奏分为“文场”与“武场”两大部分,二者在《碰碑》中既有分工又紧密配合,共同服务于“忠烈赴死”的核心情感表达。

文场伴奏:以柔衬悲,勾勒人物心境
文场伴奏以管弦乐器为主,负责唱腔的托腔保调、情绪渲染以及场景氛围的铺陈。《碰碑》中的文场乐器以京胡为核心,辅以京二胡、月琴、三弦、笛子等,通过音色的融合与旋律的起伏,细腻刻画杨继业被困两狼山、孤立无援时的苍凉心境。
京胡作为京剧文场的“主心骨”,在《碰碑》中承担着主导旋律的重要任务,其定弦为西皮调的“la-mi”或二黄调的“sol-re”,根据杨继业的唱腔情绪灵活转换,在杨继业回忆杨家将世代忠心、报国无怨的二黄慢板唱段中,京胡多用低音把位,弓法沉稳,旋律如泣如诉,与唱腔中“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血战沙场几十年功高”的词句相呼应,将英雄迟暮的悲愤与无奈娓娓道来,而当唱腔转入“盼兵不到粮草尽,老眼昏昏盼儿还”的散板时,京胡则采用“擞音”技巧,通过琴弦的细微震动模拟风雪呼啸之声,既暗示了两狼山的环境恶劣,又强化了杨继业内心的焦灼与绝望。
京二胡作为京胡的“补充音色”,在《碰碑》中多以中音区融入,其柔和的音色既能缓冲京胡的高亢,又能丰富旋律的层次感,如在杨继业得知援兵被辽军埋伏时的二黄导板中,京二胡与京胡形成“高低应和”,京胡拉出长音,京二胡则以短促的音符点缀,如同英雄内心的波澜翻涌,月琴与三弦则负责节奏支撑,月琴的清脆与三弦的浑厚相得益彰,通过“轮指”“扫弦”等技法,为唱腔提供稳定的律动,使悲情的旋律不失京剧音乐的“骨力”,笛子在《碰碑》中虽非主奏,但在表现“风雪夜”的场景时,以其清越的音色吹奏出快速的花舌音,模拟风雪交加的声响,与文场其他乐器共同营造出“天寒地冻、孤军奋战”的意境。
武场伴奏:以刚烘托,强化戏剧冲突
武场伴奏以打击乐器为主,包括板鼓、大锣、小锣、铙钹等,其核心功能是控制节奏、烘托气氛、配合身段动作,在《碰碑》中通过“刚猛”与“沉寂”的对比,将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板鼓是武场的“指挥中枢”,通过鼓板的“点击”“滚奏”等技巧,引导唱腔的启承转合与剧情的节奏变化,在《碰碑》开场,杨继业率部被困,板鼓先以“慢长锤”奠定压抑的基调,鼓点由疏到密,如同心跳逐渐加速,暗示危机临近;当杨继业决定突围时,鼓点转为“急急风”,节奏密集而急促,配合演员的“趟马”身段,凸显战场的紧张与杨继业的决绝。
大锣、小锣、铙钹则通过不同的音色与力度,强化情感表达,大锣声音洪亮,多用于表现“悲壮”或“激烈”的场景:在杨继业唱到“碰碑”二字时,大锣以“一击”收尾,声音如金石炸裂,既象征英雄的陨落,也震撼观众心灵;小锣声音清脆,多用于表现“细节”或“转折”,如杨继业发现身边只剩老将焦赞时,小锣轻击两下,配合演员的“惊诧”眼神,凸显孤立无援的绝望,铙钹则以“镲片”的碰撞声制造“冲突感”,如在辽军围攻的场面中,铙钹与大锣、小锣齐鸣,形成“金鼓齐鸣”的音响效果,将戏剧张力推向顶点。
值得一提的是,《碰碑》中“碰碑”一场的武场处理极具特色,在杨继业撞向石碑的瞬间,武场乐器突然“静默”片刻,随即大锣以“闷击”(即用锣槌轻击锣心)发出低沉的“嗡——”声,如同英雄生命的最后一丝叹息;紧接着,小锣以“单击”收尾,声音渐弱,象征英雄的消逝,这种“以静衬动”的处理,比单纯的喧闹更具悲剧感染力,让观众在“无声”与“有声”的转换中感受到震撼。
文武场配合:悲情交响,共塑英雄形象
《碰碑》的伴奏魅力,在于文场与武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通过节奏、音色、情绪的默契配合,共同构建起完整的艺术表达,在杨继业临终前的“二黄散板”唱段中,文场京胡以悠长而苍凉的旋律托起唱腔,武场则以板鼓的“轻点”和小锣的“弱击”作为点缀,如同雪花飘落,既不喧宾夺主,又强化了“风雪夜归人”的凄凉感;而当唱腔达到高潮时,武场大锣突然加入,与文场的京胡旋律形成“强强联合”,将英雄的悲愤与不屈推向极致。

这种配合还体现在“唱做结合”中,杨继业的“甩髯”“指碑”“踉跄”等身段动作,均需伴奏的精准呼应:如“甩髯”时,小锣轻击一声,配合髯口的甩动;“指碑”时,板鼓的“重击”突出动作的力度;“踉跄倒地”时,文场旋律骤然下行,武场大锣“闷击”,三者共同完成“英雄陨落”的瞬间定格。
京剧《碰碑》伴奏乐器及作用简表
| 乐器类别 | 乐器名称 | 在《碰碑》中的作用 |
|---|---|---|
| 文场 | 京胡 | 主奏乐器,通过弓法、把位变化托腔保调,主导旋律情绪(如苍凉、悲愤)。 |
| 文场 | 京二胡 | 补充中音区,与京胡形成高低应和,丰富旋律层次。 |
| 文场 | 月琴、三弦 | 节奏支撑,通过弹拨技法稳定唱腔律动,增强音乐的“骨力”。 |
| 文场 | 笛子 | 色彩辅助,模拟风雪声等环境音效,营造场景氛围。 |
| 武场 | 板鼓 | 指挥核心,控制节奏、启停,引导剧情与表演的节奏变化。 |
| 武场 | 大锣 | 烘托悲壮、激烈情绪,关键处“一击”强化戏剧冲突(如“碰碑”瞬间)。 |
| 武场 | 小锣 | 点缀细节,配合身段动作(如惊诧、绝望),音色清脆轻巧。 |
| 武场 | 铙钹 | 制造冲突感,与其他打击乐器配合形成“金鼓齐鸣”的音响效果,增强戏剧张力。 |
相关问答FAQs
Q1:京剧《碰碑》中,京胡的定弦为何常选择二黄调,而非西皮调?
A1:二黄调的旋律特点更适合表现“悲愤、苍凉、沉郁”的情绪,其定弦为“sol-re”,音域较低,弓法上多用“连弓”与“揉弦”,能够细腻刻画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时的英雄末路之感,相比之下,西皮调的旋律更为明快流畅,多表现“喜悦、激昂”的情绪,与《碰碑》的悲剧基调不符,通过二黄调的定弦与演奏,京胡能更好地与杨继业的唱腔、表演相融合,强化悲剧感染力。
Q2:武场乐器在“碰碑”一戏中,如何通过“静默”与“声响”的对比强化悲剧效果?
A2:“静默”与“声响”的对比是武场渲染悲剧的重要手法,在杨继业决定碰碑前,武场乐器突然“静默”数秒,营造“万籁俱寂”的氛围,让观众聚焦于人物内心的挣扎;随后,大锣以“闷击”发出低沉的“嗡——”声,如同英雄生命的最后一丝叹息;紧接着,小锣以“单击”收尾,声音渐弱直至消失,象征英雄的消逝,这种“先静后响、再归于静”的处理,避免了单纯喧闹的直白,通过“留白”让观众在回味中感受悲剧的震撼力,比持续的高强度音响更具艺术张力。